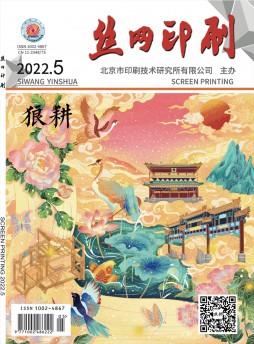印刷文化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shù)篇優(yōu)質(zhì)印刷文化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lái)啟發(fā),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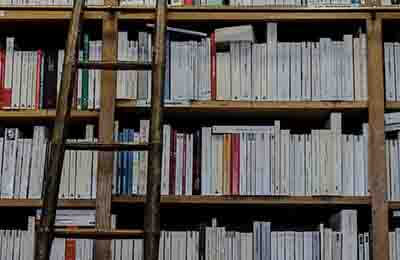
第1篇
關(guān)鍵詞:傳教士;印刷媒體;文字傳教
中圖分類號(hào):G239.29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hào):1673-291X(2017)02-0184-02
我國(guó)近、現(xiàn)代的社會(huì)變革、經(jīng)濟(jì)發(fā)展、文化活躍,無(wú)一不是由于廣泛流傳的新興出版物所引起與促成的。受時(shí)局所迫,早期來(lái)華傳教士無(wú)法直接傳教,他們致力于各項(xiàng)文化活動(dòng),客觀上推動(dòng)了中國(guó)近代教育、出版、印刷和醫(yī)學(xué)等各項(xiàng)事業(yè)的發(fā)展。但他們的終極目標(biāo)都是為了傳播基督教,并且在傳播的過(guò)程中流露出西方文明優(yōu)于中國(guó)文明的心態(tài)。
一、早期來(lái)華的傳教士對(duì)印刷媒體的重視
最先把西方鉛活字印刷術(shù)傳到中國(guó)的是 19 世紀(jì)初期英國(guó)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他是基督教新教派到中國(guó)傳教的第一人。由于當(dāng)時(shí)我國(guó)實(shí)行禁教政策,根據(jù)清政府“禁止西人傳教,查出論死,入教者發(fā)極邊”的命令,因此,早期來(lái)華的傳教士在中國(guó)的傳教工作并沒(méi)有取得什么進(jìn)展。后來(lái),馬禮遜和其助手英國(guó)人米憐認(rèn)識(shí)到,僅靠口頭說(shuō)教并不能對(duì)中國(guó)深厚的儒家文化造成什么沖擊,而且在各方面都會(huì)受到中國(guó)官吏的阻撓,因此,他們向倫敦差會(huì)提出了一系列傳教方針,其中之一就是出版書籍報(bào)刊。在傳教士看來(lái),文字傳教是向中國(guó)傳播基督福音的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米憐曾說(shuō)道:“不管以何種洗練的語(yǔ)言來(lái)表達(dá),在傳播人或有關(guān)神的知識(shí)上,印刷媒體顯然要比其他媒體更占優(yōu)勢(shì)。作為加深理解的手段,中文書籍之重要性也許要比其他傳播媒體還要大。”英國(guó)浸禮會(huì)傳教士李提摩太也認(rèn)為,印刷的書刊比口頭的講道對(duì)中國(guó)士大夫更合適,借文字來(lái)宣傳基督教比其他方法較能直接接觸更多的人,也接觸的更快、更有效。為了傳教的需要,馬禮遜派米憐和中國(guó)人梁發(fā)、蔡高到馬六甲設(shè)立印刷所,印刷宗教宣髕罰并在 1819 年第一次用活字印成了中文《圣經(jīng)》,這也是最早的中文新式鉛印書籍。1843 年,英國(guó)倫敦會(huì)傳教士麥都思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墨海書館,該書館使用以牛為動(dòng)力的機(jī)器印制圖書,這是外國(guó)在中國(guó)設(shè)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機(jī)構(gòu),也是中國(guó)近代第一家鉛印出版機(jī)構(gòu)。另外,該館出版的《六合叢刊》也是我國(guó)最早的鉛印雜志之一。
在近代基督教傳教士來(lái)華之前,中國(guó)還沒(méi)有一本公開刊行、能供公眾閱讀的中文圣經(jīng)譯本,這就成為傳教士來(lái)華傳教首先要解決的問(wèn)題,也是傳教士建立出版印刷機(jī)構(gòu)的最重要的原因。其次,傳教士要與中國(guó)的官員接觸,深入民間傳道,就要精通中文,而要翻譯、出版中文圣經(jīng)和各種宗教讀物,就需要借助字典、詞匯等工具書才能完成。當(dāng)然,這也同國(guó)內(nèi)禁教政策有關(guān),在歐洲會(huì)漢語(yǔ)的人極少,而在中國(guó),教授漢語(yǔ)是一件殺頭的事情,所以,要讓后人到中國(guó)傳教或通商取得更多的語(yǔ)言便利,在華傳教士有責(zé)任編撰華英工具書。再次,在近代來(lái)華的傳教士中,大多是受過(guò)高等教育的人,他們來(lái)到中國(guó)的目的,一個(gè)是傳教,另一個(gè)就是宣傳西方的科學(xué)技術(shù)。早在 18 世紀(jì),法國(guó)的傳教士就編纂了大量關(guān)于中國(guó)古文化的著作,而中國(guó)古代哲學(xué)、倫理學(xué)以及文化、藝術(shù)早期在歐洲的傳播,也為歐美國(guó)家的民主革命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近代,隨著傳教士所設(shè)立的出版機(jī)構(gòu)出版的大量關(guān)于西方學(xué)術(shù)、文化和科技著作在中國(guó)的傳播,對(duì)于處在轉(zhuǎn)型期的中國(guó)來(lái)說(shuō),也起了很大促進(jìn)作用。
二、來(lái)華的傳教士的文字播道
中國(guó)是一個(gè)文化悠久、長(zhǎng)期閉關(guān)自守的國(guó)家,西方傳教士深知,在文化上要想同化、征服這個(gè)國(guó)家,只能采用最簡(jiǎn)易、最廣泛、最能改變?nèi)藗冹`魂的工具――出版報(bào)刊來(lái)征服中國(guó)人。因?yàn)檫@是“一個(gè)更迅速的辦法”,“別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變頭腦,而文字宣傳則可以使成百萬(wàn)的人改變頭腦”。英國(guó)傳教士李提摩太在《給英駐上海領(lǐng)事白利蘭的信》中說(shuō):“只要控制住在中國(guó)出版的主要報(bào)刊,我們就控制到了這個(gè)國(guó)家的頭和背脊骨。”帝國(guó)主義者為了從精神上奴役中國(guó)人民,他們?cè)谥袊?guó)建立出版機(jī)關(guān)。近代西方傳教士在中國(guó)設(shè)立的出版機(jī)構(gòu)大致可以分為三種,即由傳教士獨(dú)立創(chuàng)辦經(jīng)營(yíng)的出版機(jī)構(gòu),如格致書室;專門出版?zhèn)鹘虉D書的出版機(jī)構(gòu),如美華書館;服務(wù)于帝國(guó)主義侵華勢(shì)力的出版機(jī)構(gòu),如廣學(xué)會(huì)。
傳教的過(guò)程可以看成是傳教士―傳教媒介―受傳者這樣一個(gè)過(guò)程。基督教新教入華以馬禮遜1807年來(lái)華為開端。馬禮遜譯《圣經(jīng)》、編字典、辦報(bào)刊、設(shè)印刷所,終其一生致力于基督教文字工作。而馬禮遜的文字傳教策略多為后來(lái)的傳教士所效仿。從傳教媒介看,當(dāng)時(shí)的傳教士所采用的除文字布道,還有通過(guò)口頭布道、教育、醫(yī)療、慈善等方式,相比之下,文字傳教更有其獨(dú)特的優(yōu)勢(shì)。第一,漢字的廣泛應(yīng)用性,使文字作品可以在大范圍內(nèi)流傳。英國(guó)傳教士米憐曾這樣說(shuō)道:“我發(fā)現(xiàn)中國(guó)的方言非常之多,而且語(yǔ)音各異,常常無(wú)法互相交談,唯一的辦法是可以寫中文字和別人交流。”第二,文字作品的滲透性可以到達(dá)傳教士所不能到達(dá)的區(qū)域。廣泛使用印刷品來(lái)傳播知識(shí),會(huì)比教師的說(shuō)教傳播得廣泛。第三,文字作品自身所具有的問(wèn)文化性可以更深刻地改變一個(gè)社會(huì)。
為了讓中國(guó)民眾接受基督教,來(lái)華傳教士試圖出版宣揚(yáng)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學(xué)知識(shí)的書刊,從觀念上改變中國(guó)人。因?yàn)榍逭南藿陶撸陆虃鹘淌吭趶V州隱居。他們發(fā)現(xiàn)中國(guó)官方直至民間有著強(qiáng)烈的天朝自大的心理,強(qiáng)烈地感受到了中國(guó)人看不起外國(guó)人的心態(tài)。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傳教士裨治文等人在1834年發(fā)起創(chuàng)辦 “益智會(huì)”。顧名思義,目的就是要向中國(guó)人傳播“實(shí)用”的知識(shí),以幫助中國(guó)取得知識(shí)進(jìn)步和社會(huì)進(jìn)步,將西方近代科學(xué)文明作為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介紹給中國(guó)人。“益智會(huì)”出版了一部分中國(guó)書籍,包括郭實(shí)獵的《古今萬(wàn)國(guó)綱鑒》、《萬(wàn)國(guó)地理全集》,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國(guó)志略》、《廣州方言中文文選》,以及后期的《東西洋考每月統(tǒng)記傳》等等。裨治文編寫的《美理哥合省國(guó)志略》是第一本中文美國(guó)史著作。裨治文在書中塑造一個(gè)可與大清媲美的富強(qiáng)、廣袤、文明的美國(guó)形象,為中國(guó)人正確認(rèn)識(shí)美國(guó)奠定了基礎(chǔ)。裨治文在書中表達(dá)了美國(guó)作為西方國(guó)家的代表,文明程度之所以不遜于中國(guó),得益于西方基督教文明。而他在書中表達(dá)了“四海為一家”的意愿,目的在于瓦解中國(guó)人的“天下”、“中國(guó)”和“四夷”觀念,使中國(guó)人拋開大中華文化優(yōu)越感而接受基督教的信仰。
傳教士利用多種方式進(jìn)行文字傳教,也使中國(guó)的文獻(xiàn)形式逐漸多樣化。近代報(bào)紙和期刊因其傳播速度快、覆蓋面廣、價(jià)格低廉的特點(diǎn)而被傳教士引入到中國(guó)。報(bào)紙和期刊在中國(guó)得到快速發(fā)展,并逐漸成為傳播領(lǐng)域的重要媒介,打破了圖書媒介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而且報(bào)紙、雜志更以通俗易懂的內(nèi)容受到廣大民眾的歡迎,推進(jìn)了大眾傳媒時(shí)代的到來(lái)。
近代西方傳教士在華所進(jìn)行的文字傳教工作,客觀上直接催生了中國(guó)新聞出版業(yè),并影響了出版業(yè)的方方面面。據(jù)梁?jiǎn)⒊段鲗W(xué)書目表》統(tǒng)計(jì),時(shí)期出版的350部西書中,外國(guó)人翻譯的139部,中外學(xué)者合作翻譯的123部,中國(guó)人翻譯的只有38部。而這些外國(guó)人大都是傳教士。隨著西學(xué)的傳播,中國(guó)的知識(shí)分子也開始主動(dòng)參與引進(jìn)西學(xué),并逐漸成為主要力量。隨著中國(guó)民族意識(shí)的覺(jué)醒,20世紀(jì)初中國(guó)民營(yíng)出版業(yè)紛紛崛起,在文化傳播上逐漸掌握了自,傳教士的作用逐漸退居次要地位。
參考文獻(xiàn):
第2篇
[關(guān)鍵詞] 錢存訓(xùn) 中國(guó)出版史 述評(píng)
[中圖分類號(hào)]G239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
1009-5853(2010)06-0011-05
錢存訓(xùn)(Tsuen-Hsuin Tsien)先生,1910年出生于江蘇省泰州市,1932年畢業(yè)于金陵大學(xué)(今南京大學(xué)),獲文學(xué)學(xué)士學(xué)位,1952年、1957年分獲美國(guó)芝加哥大學(xué)圖書館學(xué)碩士學(xué)位和博士學(xué)位。錢先生赴美前曾先后擔(dān)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學(xué)圖書館館長(zhǎng)、上海交通大學(xué)圖書館副館長(zhǎng)、北京圖書館南京及上海辦事處主任等職。赴美后曾任美國(guó)芝加哥大學(xué)東亞語(yǔ)言文明系兼圖書館學(xué)研究院教授、遠(yuǎn)東圖書館館長(zhǎng)和夏威夷大學(xué)客座教授等職,現(xiàn)任芝加哥大學(xué)東亞語(yǔ)言文明系榮譽(yù)教授、東亞圖書館榮譽(yù)館長(zhǎng)、英國(guó)李約瑟科技史研究所榮譽(yù)研究員、美國(guó)中國(guó)出版服務(wù)公司董事長(zhǎng)等職。
錢存訓(xùn)先生是海內(nèi)外聞名的中國(guó)出版史研究專家,著有《書于竹帛》《中國(guó)紙和印刷文化史》《中國(guó)古代書籍紙墨及印刷術(shù)》《東西文化交流論叢》《留美雜憶》等著述。錢先生對(duì)自己的研究曾有一個(gè)總結(jié):“我的研究范圍主要環(huán)繞兩大主題:中國(guó)圖書印刷史和中外文化交流,而兩者的結(jié)合,從高度和比較的觀點(diǎn)出發(fā),所得出的結(jié)論便成為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特色和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在中國(guó)出版史這一研究領(lǐng)域,錢先生在海外為宣傳和推廣中國(guó)文化做出了杰出貢獻(xiàn)。其具體成就表現(xiàn)在下列方面。
1 對(duì)紙發(fā)明前的中國(guó)文字記錄及對(duì)中國(guó)書籍制度的影響做了全面研究
在印刷術(shù)發(fā)明前,世界各國(guó)的文字記錄可謂豐富多彩。中國(guó)也是如此。王國(guó)維先生《簡(jiǎn)牘檢署考》(1912)、羅振玉與王國(guó)維合著的《流沙墜簡(jiǎn)》(1914)等對(duì)簡(jiǎn)牘實(shí)物與文獻(xiàn)記述進(jìn)行了研究,但并沒(méi)有涉及書籍制度的所有方面。《書于竹帛》的出版,對(duì)紙發(fā)明前的中國(guó)文字記錄做了全面研究,探討了紙前記錄方式對(duì)中國(guó)書籍制度產(chǎn)生的影響,填補(bǔ)了這一領(lǐng)域的空白。
《書于竹帛》的底稿是錢存訓(xùn)先生1957年提交給芝加哥大學(xué)的博士論文《印刷發(fā)明前的中國(guó)文字記錄和圖書》(ThePre-printingRecordofChina:A Study of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Inscripdons andBooks),經(jīng)過(guò)修改后以《書于竹帛》(WrittenonBambooand Silk: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Books andInscriptions)為名由芝加哥大學(xué)出版社于1962年正式出版。該書共分9章。第一章是《緒論》,對(duì)中國(guó)古代文字記錄方式進(jìn)行了總體上的介紹。第二章是《甲骨文》,介紹甲骨文的起源和性質(zhì)、甲骨文的形勢(shì)和契刻、卜辭的內(nèi)容及排列等。第三章是《金文和陶文》,對(duì)金文和陶文的性質(zhì)、用途、款式等進(jìn)行研究。第四章是《玉石刻辭》,對(duì)石鼓文和古代刻石、玉器刻辭等進(jìn)行研究。第五章是《竹簡(jiǎn)和木牘》,對(duì)簡(jiǎn)牘的形式、整治、行格和書體、編裝方式等進(jìn)行了研究。第六章是《帛書》,對(duì)帛書的起源、發(fā)現(xiàn)、材料、形式等進(jìn)行研究。第七章是《紙卷》,對(duì)紙的發(fā)明與改進(jìn)、古紙的材料和制作、卷軸制度等進(jìn)行研究。第八章是《書寫工具》,對(duì)毛筆、墨、書刀等工具進(jìn)行研究。第九章是《結(jié)論》,對(duì)中國(guó)書籍的起源與發(fā)展、書寫和復(fù)制技術(shù)、文字的演化等問(wèn)題進(jìn)行研究。該書英文本出版后,受到西方學(xué)術(shù)界的廣泛好評(píng),除不斷重印外,還被譯成中、日、韓等其他文字。2004年,該書的英文第二版也再次由芝加哥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
《書于竹帛》指出:“古代文字之刻于甲骨、金石及印于陶泥者,皆不能稱之為‘書’。書籍的起源,當(dāng)追溯至竹簡(jiǎn)和木牘,編以書繩,聚簡(jiǎn)成篇,如同今日的書籍冊(cè)頁(yè)一般。在紙發(fā)明以前,竹、木不僅是最普遍的書寫材料,且在中國(guó)歷史上被采用的時(shí)間,亦較諸其他材料更為長(zhǎng)久,甚至在紙發(fā)明以后數(shù)百年間,簡(jiǎn)牘仍繼續(xù)用作書寫。”“竹簡(jiǎn)和木牘是中國(guó)最早的書寫材料,在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上,簡(jiǎn)牘制度有其極為重要和深遠(yuǎn)的影響。不僅中國(guó)文字的直行書寫和自右向左的排列順序淵源于此,即使在紙張和印刷術(shù)發(fā)明之后,中國(guó)書籍的單位、術(shù)語(yǔ),以及版面上的所謂‘行格’的形式,也是根源于簡(jiǎn)牘制度而來(lái)。”這一觀點(diǎn),理清了書籍的源頭,可以避免將早期“書籍”的范圍無(wú)限擴(kuò)大。
目前,《書于竹帛》已有4個(gè)不同的中文譯本。1975年,根據(jù)周寧森博士譯稿修訂的《中國(guó)古代書史》,由香港中文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1981年再版:1987年,由鄭如斯教授增補(bǔ)的《印刷發(fā)明前的中國(guó)書和文字記錄》,由北京印刷工業(yè)出版社出版;1996年,臺(tái)灣漢美圖書公司以《書于竹帛》為名,出版了該書的繁體字版;2002年,上海的上海書店出版社也以《書于竹帛:中國(guó)古代的文字記錄》為題,出版了該書的第四個(gè)增訂本。這些不同的譯本,充分顯示了該書具有的不朽生命力。尤其是“世紀(jì)文庫(kù)”本的《書于竹帛》和芝加哥大學(xué)出版社第二版英文本“Written onBambooand Silk”,以近年出土的考古實(shí)物為主,補(bǔ)充了新發(fā)現(xiàn)的殷墟以外和周初的甲骨、戰(zhàn)國(guó)及秦漢墓中出土的竹簡(jiǎn)、帛書、各類古地圖、敦煌遺書中最早的抄本等內(nèi)容,更使該書具有新的生命力。
此外,收錄在《中國(guó)古代書籍紙墨及印刷術(shù)》(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版)中的《漢代書刀考》,對(duì)簡(jiǎn)牘時(shí)期整治書寫材料和刪改文字的書刀做了全面考證與分析,認(rèn)為“書刀的功用在刪除寫錯(cuò)的簡(jiǎn)面,以便改正重寫,或者削去舊簡(jiǎn)已經(jīng)書寫的舊面,取得新的簡(jiǎn)面,以便再行書寫”,從而糾正了以往文獻(xiàn)中認(rèn)為書刀或刀削是簡(jiǎn)策上刊刻文字的工具這一錯(cuò)誤說(shuō)法。2對(duì)中國(guó)紙和印刷術(shù)的發(fā)明與發(fā)展做了全面研究
在《書于竹帛》一書的基礎(chǔ)上,錢先生應(yīng)英國(guó)劍橋大學(xué)李約瑟(Joseph Needham)先生之約,為李氏主編的《中國(guó)科學(xué)技術(shù)史》撰寫《造紙和印刷》分冊(cè),1985年由劍橋大學(xué)出版社正式出版。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與科學(xué)出版社出版了劉祖慰教授的譯本《中國(guó)科學(xué)技術(shù)史?紙和印刷》。1995年,臺(tái)北商務(wù)印書館出版了劉拓、汪劉次昕的譯本《造紙和印刷》。2004年,該書由北京大學(xué)鄭如斯教授編訂、增加了新材料后由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以《中國(guó)紙和印刷文化史》為名出版。
《中國(guó)紙與印刷文化史》堪稱《書于竹帛》的姊妹篇。該書對(duì)印刷術(shù)發(fā)明后的中國(guó)書籍和文字記錄進(jìn)行研究。全書十章。第一章是《緒論》,從宏觀上對(duì)造紙術(shù)和印刷術(shù)的起源和發(fā)展、中國(guó)發(fā)明造紙和印刷術(shù)的
原因等進(jìn)行介紹。第二章至第四章是有關(guān)紙的研究。第二章是《紙的性質(zhì)和演變》,對(duì)紙的定義、造紙的起源與發(fā)展等問(wèn)題進(jìn)行研究。第三章是《造紙的技術(shù)與方法》,對(duì)造紙的原料、工序等進(jìn)行介紹。第四章是《紙的用途和紙制品》,對(duì)各種紙的用途進(jìn)行介紹。第五章至第七章是對(duì)印刷術(shù)的研究。第五章是《中國(guó)印刷的起源與發(fā)展》,對(duì)印刷術(shù)的發(fā)明及歷展進(jìn)行宏觀介紹。第六章是《中國(guó)印刷的技術(shù)和程序》,對(duì)雕版印刷的材料和工藝、活字版的種類和方法、中國(guó)書的版式和裝訂等進(jìn)行了研究。第七章是《中國(guó)印刷的藝術(shù)和圖繪》,對(duì)木刻版畫、年畫、套色復(fù)印技術(shù)等進(jìn)行了研究。第八章至第十章是有關(guān)紙與印刷的傳播史。第八章是《紙與印刷術(shù)的西傳》,談?wù)摷埮c印刷術(shù)傳向西方的過(guò)程,以及西方現(xiàn)代印刷術(shù)起源的中國(guó)背景。第九章是《紙與印刷術(shù)的東漸和南傳》,談?wù)摷埮c印刷術(shù)傳向朝鮮、日本、越南等國(guó)的過(guò)程。第十章是《紙與印刷術(shù)對(duì)世界文明的貢獻(xiàn)》,探討紙與印刷術(shù)對(duì)中國(guó)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作用。
《中國(guó)紙與印刷文化史》是世界范圍內(nèi)第一部全面探討紙和印刷術(shù)的專門著作。雖然此前已有孫毓修的《中國(guó)雕板源流考》(1908)、賀圣鼐的《近現(xiàn)代印刷術(shù)》(1933)、美國(guó)卡特的《中國(guó)印刷術(shù)的發(fā)明及其西傳》(1925)、日本中山久四郎著的《世界印刷通史?支那篇》(1930)等書問(wèn)世,但錢先生的這一著作,無(wú)論在廣度還是深度上都要比上述著作深入。
《中國(guó)古代書籍紙墨及印刷術(shù)》(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版)收錄了一些因篇幅受限而未能在上述書籍中展開論述的文章。如《紙的起源新證》,對(duì)1975―1976年間湖北云夢(mèng)縣睡虎地戰(zhàn)國(guó)秦墓出土竹簡(jiǎn)中所見的“紙”字做了考證,認(rèn)為它同1935年長(zhǎng)沙出土的戰(zhàn)國(guó)時(shí)代漆馬內(nèi)的紙?zhí)ィ梢宰鳛閼?zhàn)國(guó)時(shí)代有紙的證據(jù)。而《現(xiàn)存最早的印刷品和雕版實(shí)物》,對(duì)1966年韓國(guó)慶州出土的《無(wú)垢凈光大陀羅尼經(jīng)》進(jìn)行了詳細(xì)分析,認(rèn)為該印本“為唐代中國(guó)所印制”。錢先生對(duì)此問(wèn)題的關(guān)注和研究,有力地駁斥了韓國(guó)有人認(rèn)為印刷術(shù)是韓國(guó)發(fā)明的論調(diào),維護(hù)了中國(guó)是印刷術(shù)發(fā)明國(guó)的國(guó)際地位。由于韓國(guó)慶州出土該經(jīng)時(shí),中國(guó)國(guó)內(nèi)正開始“”,對(duì)韓國(guó)的這一發(fā)現(xiàn)一無(wú)所知。1979年,錢先生回國(guó)訪問(wèn)時(shí),特意將他自己收集的該經(jīng)的復(fù)印本全份和有關(guān)報(bào)道、研究資料等贈(zèng)送給上海圖書館保存,以供國(guó)內(nèi)專家研究,更體現(xiàn)了錢先生博大的胸懷。
3 從世界文明比較的高度,闡述了中國(guó)出版與中華文明的關(guān)系
錢先生國(guó)學(xué)修養(yǎng)深厚,又受過(guò)嚴(yán)格的西學(xué)訓(xùn)練,因此,善于將中國(guó)出版史放在廣闊的社會(huì)背景之中進(jìn)行探討,通過(guò)國(guó)際比較,揭示文字記錄與中西文明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這種比較方法,大大拓寬了出版史的研究路徑。
在《書于竹帛》一書中,錢先生特別提到中國(guó)文字的排列方式。中國(guó)文字的豎排、自右及左與西方文字的橫排、自左及右完全不同。錢先生在《書于竹帛》一書中認(rèn)為:“這種直行書寫的原因雖不可確考,但可推測(cè)這一特點(diǎn)應(yīng)和中國(guó)文字的構(gòu)造、書寫材料、應(yīng)用工具以及生理和心理等因素有關(guān)。中國(guó)古代的象形文字,如人體、動(dòng)物、器皿,大多縱向直立而非橫臥;毛筆書寫的筆順,大多是從上到下;竹木材料的紋理以及狹窄的簡(jiǎn)策,只能容單行書寫等等,都是促成這種書寫順序的主因。至于從右到左的排列,大概是因?yàn)橛米笫謭?zhí)簡(jiǎn)、右手書寫的習(xí)慣,便于將寫好的簡(jiǎn)策順序置于右側(cè),由遠(yuǎn)而近,因此形成從右到左的習(xí)慣。這一解釋,合乎情理,已被學(xué)術(shù)界廣泛接受。錢先生在《上海版新序》別指出:“中國(guó)古代的書籍和文字記錄的多姿多彩、源遠(yuǎn)流長(zhǎng),是中國(guó)民族精神之所寄,也是世界文明有的奇跡。可是由于近代中國(guó)所受的外侮和屈辱,使中國(guó)人對(duì)自己固有的文化傳統(tǒng)喪失自信而盲目自貶,甚至現(xiàn)在還有人認(rèn)為廢除漢字采用拼音是文字演進(jìn)的規(guī)律和迎合世界的潮流,卻沒(méi)有深思漢字的特殊功能。假使沒(méi)有漢字形體所獨(dú)具的延續(xù)性和凝固性相維護(hù)而采用拼音文字,中國(guó)早已成為許多以方言立國(guó)而分崩離析的國(guó)家了。近代歐洲各民族以方言立國(guó),足資證明。”錢先生的告誡,對(duì)保存中國(guó)傳統(tǒng)出版文化具有振聾發(fā)聵的作用。
世界上其他國(guó)家也很早就出現(xiàn)了印章,但為什么沒(méi)有發(fā)明印刷術(shù)?錢先生同樣從比較的高度對(duì)這一問(wèn)題進(jìn)行了探討:“中國(guó)很早就應(yīng)用印刷術(shù)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很早就發(fā)明了紙,對(duì)印章和墨拓的運(yùn)用奠定了印刷技術(shù)上的基礎(chǔ)。漢字作為表意文字的書寫復(fù)雜性造成對(duì)機(jī)械復(fù)制的需求,由于科舉而需要標(biāo)準(zhǔn)的儒家經(jīng)典,以及手工抄寫無(wú)法滿足社會(huì)對(duì)大量佛經(jīng)復(fù)制品的需要。在西方,紙到了很晚的時(shí)候才傳入,印章沒(méi)有移用作復(fù)印的用途,拓印到了19世紀(jì)才傳入,印刷工人被形形的行會(huì)所束縛,字母拼寫文字的相對(duì)簡(jiǎn)易性減輕了對(duì)機(jī)械復(fù)印的需求。……在歐洲不存在諸如和佛教有關(guān)的那種對(duì)大量復(fù)印品的需要作為動(dòng)因;西方對(duì)書籍的需要手工抄寫就能滿足。直至15世紀(jì)中葉所有因素才有所改變”。中國(guó)的印刷術(shù)和西方印刷術(shù)在社會(huì)發(fā)展中產(chǎn)生了不同作用,其原因何在?錢先生認(rèn)為:“在西方,印刷術(shù)同時(shí)激發(fā)理智思潮,促進(jìn)民族語(yǔ)言和文字的發(fā)展以及在文學(xué)上的應(yīng)用,并鼓勵(lì)了民族主義和建立新興民族國(guó)家的行動(dòng)。相反,在中國(guó),印刷術(shù)幫助書寫文字的連續(xù)性和普遍性,成為保持文化傳統(tǒng)的重要工具。”此外,“中國(guó)的印刷事業(yè)一般由政府機(jī)構(gòu)或私人主持,重在‘傳先哲精蘊(yùn),啟后學(xué)困蒙’,并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歐洲的印刷業(yè)則多為謀利經(jīng)營(yíng),因此形成了勢(shì)力強(qiáng)大的出版工業(yè)。這些不同的動(dòng)機(jī),使得印刷術(shù)的發(fā)展與應(yīng)用對(duì)社會(huì)產(chǎn)生不同的影響”。錢先生的這些論述,為更好地理解中國(guó)印刷術(shù)對(duì)社會(huì)的作用,提供了一個(gè)新的視角。
在《近代譯書對(duì)中國(guó)現(xiàn)代化的影響》中,錢先生采用文獻(xiàn)計(jì)量學(xué)的方法,對(duì)16世紀(jì)末開始的西書中譯活動(dòng)進(jìn)行研究,分析了“譯書在中國(guó)近代史上所反映出來(lái)的西方文化對(duì)中國(guó)現(xiàn)代化產(chǎn)生的影響”。通過(guò)分析,發(fā)現(xiàn)“人文和社會(huì)科學(xué)在過(guò)去的譯品中占主要地位,其總數(shù)達(dá)70%,而自然科學(xué)和應(yīng)用科學(xué)僅占27%。……翻譯的素材代表25個(gè)國(guó)家以上的著述,以英、日、俄文的作品為最多,其中有些是轉(zhuǎn)譯而非譯自原文……。這一結(jié)論,也有助于了解中國(guó)近代文化的形成過(guò)程以及出版在近代社會(huì)轉(zhuǎn)型中的作用。
4 指導(dǎo)了一批從事中國(guó)出版史方面研究的博碩士論文,豐富了中國(guó)出版史的研究
錢先生在身體力行從事中國(guó)出版史研究的同時(shí),還在芝加哥大學(xué)指導(dǎo)了一批博碩士生從事中國(guó)出版史研究,寫成了多篇研究中國(guó)出版史的博碩士學(xué)位論文。這些論文,涉及中國(guó)出版史研究的多個(gè)層面,豐富了海外的中國(guó)出版史研究。
在博士論文方面,潘銘粲(Poon Ming-sun)1979年完成的博士學(xué)位論文“Books andPrinring in SungChina,960-1279”(《宋代圖書印刷史》),對(duì)宋代圖書印刷史進(jìn)行了研究。許麗霞(Lee-Hsia Hsu Ting)
1969年完成的博士學(xué)位論文GovernmentControlofthePressinModemChina,1900-1949(《現(xiàn)代中國(guó)之出版自由》),就晚清和民國(guó)政府對(duì)新聞出版業(yè)的管理進(jìn)行了專門研究。該文1974年由哈佛大學(xué)東亞研究中心正式出版。蔡武雄(DavidTsai)1977年完成的博士論文A Study of Chinese Government Publications,1912-1949)(《中國(guó)政府公報(bào)研究,1912-1949》),對(duì)民國(guó)政府出版的政府公報(bào)進(jìn)行了研究。何凱立(Herbeit Hoi-Lap Ho)1979年完成的博士學(xué)位論文Protestant Missionary Publications in Modern China1912―1949:A studyoftheirprograms operations andtrends,對(duì)1912-1949年間在華傳教士的角色和活動(dòng)、傳教士創(chuàng)辦的出版機(jī)構(gòu)歷史及其組織、出版物的內(nèi)容及其特色等作了探討。該論文1988年由香港中國(guó)基督教研究中心(Chinese Church Research Centre)出版。2004年由陳建明、王再興翻譯為《基督教在華出版事業(yè)(1912―1949)》,中文本由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
第3篇
【關(guān)鍵詞】 西安理工大學(xué);印刷包裝工程學(xué)院;中德雙學(xué)歷;學(xué)位授予
隨著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大學(xué)對(duì)于知識(shí)的發(fā)現(xiàn)、研究、傳播起到越來(lái)越重要的作用。大學(xué)的發(fā)展推動(dòng)著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社會(huì)進(jìn)步,同時(shí)市場(chǎng)發(fā)育和社會(huì)需要也對(duì)大學(xué)的發(fā)展產(chǎn)生越來(lái)越大的影響。
高等學(xué)校的國(guó)際化特征是他從中世紀(jì)創(chuàng)建初始就具有的特性,并且隨著世界經(jīng)濟(jì)全球化和人才資金的國(guó)際流動(dòng),表現(xiàn)出新的形式,具有嶄新的內(nèi)容。這種高校國(guó)際化的發(fā)展有利于發(fā)展高等教育的社會(huì)中心地位,有利于高校教育體制的變革和思想觀念的變更。通過(guò)開展國(guó)際交流與合作,能起到不斷優(yōu)化教育資源和教育條件的作用。隨著國(guó)家經(jīng)濟(jì)文化的發(fā)展,留學(xué)生教育事業(yè)開始快速發(fā)展積極踐行擴(kuò)大規(guī)模、優(yōu)化結(jié)構(gòu) 、規(guī)范管理、保證質(zhì)量的發(fā)展方針,加強(qiáng)對(duì)國(guó)際交流學(xué)生的研究意義重大。[1]
西安理工大學(xué)與德國(guó)斯圖加特媒介大學(xué)友好合作歷史開始于1985年,1999年簽署了共同培養(yǎng)中德留學(xué)生計(jì)劃的協(xié)議。西安理工大學(xué)印刷工程專業(yè)創(chuàng)建于1974年,是我國(guó)成立最早的印刷工程本科專業(yè),1993年取得國(guó)內(nèi)首家印刷工程碩士學(xué)位授予權(quán)。德國(guó)斯圖加特媒介大學(xué)(Hochschule der Medien Stuttgart)是世界著名的印刷媒體領(lǐng)域高校,其與印刷相關(guān)的歷史可追溯到1853年。西安理工大學(xué)印刷包裝工程學(xué)院在順應(yīng)時(shí)展需要的情況下,開始了中德兩國(guó)雙學(xué)歷學(xué)生培養(yǎng)工作的探索。經(jīng)過(guò)幾十年的摸索,已經(jīng)從普通本科生的培養(yǎng)慢慢過(guò)渡到高水平的研究生培養(yǎng)。
研究生教育是現(xiàn)行教育培養(yǎng)機(jī)制中的最高環(huán)節(jié),它重點(diǎn)在于培養(yǎng)人才的科學(xué)研究才能,它是高等教育發(fā)展的重點(diǎn)。由于研究生具有培養(yǎng)周期時(shí)間短,與國(guó)民經(jīng)濟(jì)發(fā)展結(jié)合容易,匹配性強(qiáng)的特點(diǎn),成為發(fā)展教育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的重點(diǎn)。在過(guò)去的十幾年間,研究生的數(shù)量有了大幅增加,但是隨著這種補(bǔ)償性數(shù)量的增加凸顯出教育質(zhì)量的問(wèn)題,研究生教育的規(guī)模已經(jīng)不是發(fā)展的重點(diǎn),如何提高研究生教育質(zhì)量已經(jīng)成為提升我國(guó)研究生教育系統(tǒng)質(zhì)量刻不容緩的問(wèn)題。
中德雙學(xué)歷碩士培養(yǎng)作為一個(gè)特殊群體,它的培養(yǎng)質(zhì)量先天存在一些問(wèn)題:①不同文化背景的學(xué)生接受同一文化背景的教育,或者同一文化背景的學(xué)生接受不同文化背景的老師教育,不管是老師與老師、學(xué)生與學(xué)生還是老師與學(xué)生之間,必然存在文化差異所帶來(lái)的各種差異。②授課教師很多是使用母語(yǔ)進(jìn)行講授專業(yè)知識(shí),課程對(duì)學(xué)生入學(xué)時(shí)的外語(yǔ)能力有較高要求。③留學(xué)生在學(xué)習(xí)上和管理上都處于邊緣化狀態(tài),很難進(jìn)入學(xué)校主流學(xué)習(xí)狀態(tài)中。[2]目前國(guó)內(nèi)許多高校對(duì)留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管理和生活管理一般都相對(duì)集中,集中學(xué)習(xí)、就餐、休閑,與中國(guó)師生的交流接觸只在上課時(shí)有短時(shí)間接觸,更多數(shù)時(shí)間都封閉在個(gè)人或同國(guó)籍學(xué)生圈子里。④中外教育在課程體系、教學(xué)模式和教學(xué)內(nèi)容差異比較大。
西安理工大學(xué)印刷包裝工程學(xué)院和德國(guó)斯圖加特媒介大學(xué)經(jīng)過(guò)多年的合作總結(jié)摸索出一套完善的選拔制度。通過(guò)層層篩選選擇出外語(yǔ)水平比較高,并且專業(yè)課學(xué)習(xí)比較好的學(xué)生相互選派,并且在出國(guó)留學(xué)前由具有留學(xué)經(jīng)驗(yàn)的老師專門進(jìn)行輔導(dǎo),有助于解決語(yǔ)言問(wèn)題。同時(shí)兩校學(xué)生的交流不僅僅局限于課堂上的課程學(xué)習(xí),均會(huì)安排社會(huì)、文化的了解,如在中方安排有漢語(yǔ)和專業(yè)漢語(yǔ)的課堂內(nèi)容講解,同時(shí)有全國(guó)印刷會(huì)議的參加等活動(dòng),從而整體提高留學(xué)生的學(xué)業(yè)、學(xué)識(shí)、知識(shí)、能力以及綜合素質(zhì)。西安理工大學(xué)一直進(jìn)行的彈性學(xué)分制,學(xué)生可以自行選擇課程和所修的學(xué)分,這樣也有利于減少中外教育上的差異,也有利于兩校互派學(xué)生的課程學(xué)習(xí)中學(xué)分的認(rèn)定。
研究生教育水平最關(guān)鍵的體現(xiàn)在于學(xué)位論文,碩士研究生的課程學(xué)習(xí)時(shí)間只占整個(gè)學(xué)習(xí)時(shí)間的三分之一,更多的是對(duì)獨(dú)立完成科研項(xiàng)目研究能力的要求,學(xué)位論文的撰寫正是這一能力的體現(xiàn)。目前中德雙學(xué)歷教育中的學(xué)位論文的評(píng)定采取在本國(guó)取得學(xué)士學(xué)位后可以在對(duì)方國(guó)家申請(qǐng)第二學(xué)歷的學(xué)士學(xué)位。
目前在國(guó)內(nèi)學(xué)位論文評(píng)定中主要針對(duì)論文中的理論應(yīng)用價(jià)值、論文的創(chuàng)新性、科學(xué)態(tài)度與寫作水平以及社會(huì)應(yīng)用價(jià)值方面進(jìn)行考察從而綜合評(píng)分。[3]針對(duì)于目前的評(píng)價(jià)體系進(jìn)一步完善申請(qǐng)中德雙學(xué)歷論文的評(píng)定方法采取的工作有:首先通過(guò)廣泛和導(dǎo)師座談,通過(guò)對(duì)全院導(dǎo)師調(diào)研,了解導(dǎo)師認(rèn)為雙學(xué)歷學(xué)生目前學(xué)位論文存在的問(wèn)題,針對(duì)這些的問(wèn)題,我們分析處理,提出一個(gè)監(jiān)控評(píng)價(jià)論文質(zhì)量體系的方法。其次,重點(diǎn)和雙學(xué)歷學(xué)生的導(dǎo)師進(jìn)行溝通,了解他們對(duì)培養(yǎng)這些學(xué)生存在的問(wèn)題,和對(duì)這些學(xué)生的期望,通過(guò)在初步建立的監(jiān)控評(píng)價(jià)論文質(zhì)量體系的方法上進(jìn)一步修訂,做出專門針對(duì)雙學(xué)歷學(xué)生的論文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同時(shí)要專門跟參加雙學(xué)歷教育的中方學(xué)生和德方學(xué)生進(jìn)行座談,了解學(xué)生在培養(yǎng)中存在的問(wèn)題和論文撰寫中存在的問(wèn)題,討論解決出現(xiàn)的問(wèn)題,進(jìn)一步完善評(píng)價(jià)論文質(zhì)量體系的方法。最終通過(guò)請(qǐng)一些專家評(píng)審雙學(xué)歷學(xué)生論文,檢驗(yàn)建立的雙學(xué)歷學(xué)生學(xué)位論文評(píng)價(jià)體系是否合適。
通過(guò)這樣的方法確定的論文評(píng)價(jià)體系比較適應(yīng)兩校目前的培養(yǎng)現(xiàn)狀。但是雙學(xué)歷教育的發(fā)展是個(gè)需要不斷探索的過(guò)程。西安理工大學(xué)印刷包裝工程學(xué)院還在不斷開拓更深層次的國(guó)際交流合作,力求在新的時(shí)期發(fā)展出一條具有特色的雙學(xué)歷教育之路。
【參考文獻(xiàn)】
[1] 戴寶印,查芳靈.芻議美國(guó)海外學(xué)歷留學(xué)生對(duì)我國(guó)發(fā)展學(xué)歷留學(xué)生的啟示[J].學(xué)術(shù)論壇,2014.10.
[2] 殷君.外國(guó)留學(xué)生學(xué)歷教育過(guò)程中的若干問(wèn)題與對(duì)策[J].高等理科教育,2007.4.
[3] 王欣,殷阿娜,段亞敏.碩士學(xué)位論文全過(guò)程質(zhì)量管理與評(píng)價(jià)方法[J].大家.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