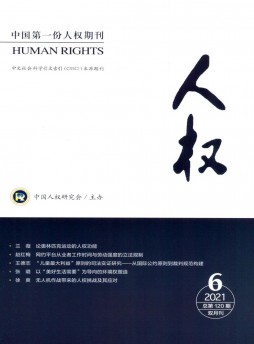人權價值實現問題分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人權價值實現問題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馬克思主義人性論認為,應在現實的社會歷史實踐當中實現人權價值,這與資本主義人性論有本質區別。后者以人性掩飾階級性,用抽象的人取代現實的人;以人性掩飾物性,用道德的人剝離實踐的人;以人性掩飾意識形態性,用超階級的人反對進行階級斗爭的人。對人性的推崇、對角色的依賴、對崇高的構建,使人權價值面臨德治化的困境。人權價值德治化的實現,依賴民眾對人權價值道德認識的提升。
[關鍵詞]人權價值;德治化;人性
人權價值(thevalueofhumanrights)是關于作為主體的人在生存和發展過程中所需要的基本價值的理論抽象,反映人權對人生存和發展需要滿足的具體價值和價值取向[1]。人權價值德治化是從道德治理的角度提出的關于實現人權價值的學術命題,涉及到人權價值的德性基礎和人權價值德治化限度問題。只有對這些問題展開論述,揭示實現人權價值的道德意蘊,才可能為人權價值的德治化找到一條現實的實現路徑。
一、人性論是實現人權價值的德性基礎嗎?
對于人性,恩格斯認為:“一切人,作為人來說,都有某些共同點,在這些共同點所及的范圍內,他們是平等的,這樣的觀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現代的平等要求與此完全不同;這種平等要求更應當是從人的這種共同特性中,從人就他們是人而言的這種平等中引申出這樣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個國家的一切公民,或一個社會的一切成員,都應當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2](P480)人性既是基于人所共有的自然屬性而使人成為群居性動物,更是基于人所特有的社會屬性而使人成其為人。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性與社會性的統一,這是人類共享人權價值的基礎。馬克思主義人性論正是從此出發,不僅把人看作是自然人與社會人的統一,更側重于從人的德性出發揭示人的自在自為的本性。中國古代就有人性善惡之說,古希臘也有關于人性善惡的討論,這都是在德性層面對人性的討論。把人的這種德性運用于人類的實踐,就出現了關于人道主義的爭論。基于人性善或惡所產生的行為、權利、思想、利益,就成為判斷或評價一定的社會制度、思想觀念、行為模式是否在尊重人,是否在踐行人道主義來維護人的權利和實現人的價值的德性標準。這是文藝復興運動時期資本主義反對封建特權的思想武器。為了推動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理論思想家把人道主義抽象化為人權、自由、平等、博愛的政治口號。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解放理論或全面發展理論不同于資本主義的人性論。后者通過人道主義者的理論幻想,試圖在人奴役人、人剝削人、人壓榨人的階級社會里,靠“理性”、“博愛”、“仁慈”、“同情”等唯心主義說教,實現人的生存和發展,這只能是哄騙和愚弄人的空話。資本主義的人性論存在三大問題:一是以人性掩飾階級性,用抽象的人取代現實的人。在資本主義社會,到處充滿著人奴役人的情況。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資產階級所要解放的“人”只是為建立自身政權而服務的政治工具。這里的“人”只能是抽象的政治人。二是以人性掩飾物性,用道德的人剝離實踐的人。不消滅人剝削人的私有制,擺脫物對人的束縛,人只能是受物奴役的從屬物。三是以人性掩飾意識形態性,用超階級的人反對進行階級斗爭的人。資產階級企圖用抽象的政治口號和空洞的道德宣傳,去解釋人的普遍的共同本性,借以反對無產階級斗爭來實現自身利益。這說明資本主義的人性論沒有找到正確實現自己所標榜的人權道路。人權價值通過對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的價值闡釋,回歸到實踐中人本身價值的實現,就能超越資本主義人性論的歷史局限性,建立起現實的人在實踐的社會關系中實現人權的價值理論體系。具體而言,要實現從資本主義的抽象人性論到人權價值的具體實現,從資本主義人性論的意識形態性到人權價值的基礎主義的轉換。從資本主義的抽象人性論到人權價值的具體實現,要解決人的發展是依據抽象的人性論,還是在具體境遇中實現人權價值的問題。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3](P18)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們看來,從來就沒有過抽象的人性,有的只是階級社會中被打上階級烙印的具體人性。人權價值的實現不能撇開這種具體的階級境遇。資產階級為了調和國內的階級矛盾,把人權說成是超越階級的可以共享的人性追求,這只是欺騙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政治伎倆。在人被人所剝削,人被物所奴役的社會現實當中,不深入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具體的、歷史的語境,無法真正找到實現具體人權價值的正確道路。要想揭開抽象人性論的虛偽面紗,就要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中揭露人作為附屬物的本質。通過消滅這種畸形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才能實現具體的人權價值。對此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任何一個存在物只有當它用自己的雙腳站立的時候,才認為自己是獨立的,而且只有當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時候,它才是用自己的雙腳站立的。”[4](P309)這里的“雙腳”就是實現人權價值的具體的實踐活動。無產階級正是在這種具體的實踐活動中粉碎了資本主義的抽象人性論。從人性論的意識形態性到人權價值的基礎主義,要解決實現人本身的價值能否跳出意識形態的爭論,而聚焦現實生活中具體的人權價值的實現。基礎主義(foundationlism)關注基本概念在感性實踐中的解釋力。人權價值對于人本身的價值而言就是一個基礎性概念。通過這個概念可以指稱和建構一個關于人本身的價值體系,用來分析人類是如何在社會關系中為自己建構一個為我而存在的價值關系。這是人權價值與作為意識形態的人性論的根本不同之處。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來都是在現實的價值關系當中來考察人權價值的實現問題。人權價值的實踐只能“是人的本質的或作為某種現實東西的人的本質的現實的生成,對人來說的真正的實現”[5](P331)。這就克服了以往只從抽象的政治口號化來認識人的本質的人性觀點,而形成了正確表達人的本質的真正認識。人既不是作為只能創造生產價值的勞動物而受物役所統治,也不是作為只能依附于其他人而存在的附屬物受人役所統治,而是在生成體現人的本質的實踐中實現人權價值的價值主體。只有跳出要么把人物化、要么把人神化、要么把人動物化的抽象爭論,才能把人理解成是為了實現人權價值而存在的有德性的價值主體。而且馬克思主義還道出,在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共同體社會中,人權價值的豐富性才能真正得以展開。這是因為在這種“已經生成的社會,創造著具有人的本質的這種全部豐富性的人,創造著具有豐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覺的人作為這個社會的恒久的現實”[6](P306)。共產主義社會就是能充分實現人權價值的共同體社會。所以《共產黨宣言》才這樣描述:“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7](P119)。在這里,作為人類存在價值的每一個個體都能實現從自然生命到社會生命、從自然價值到人權價值的雙重實現。天賦人權說認為人權是人與生俱來的,這是從自然的角度對人類自然生命的肯定。它忽略的一點是,只有被人類意識到、被人類言說、被人類實踐、被人類實現的權利才能納入到人權的范疇體系當中。人類之所以能超越一般性的動物,是因為人類的生命不僅僅是自然生命,更是能實現人權價值的社會生命。這是一種能支配本能、自然命運的社會屬性。人類正是在其所創造的社會關系中來實現自然價值。這一自然價值被打上了社會關系的烙印,從而被轉化為人權價值。人權價值內涵著人的雙重生命展現形式。一是作為自然人而具有的自然生命(本能的動物性生命),是必須在社會關系中超越的自然屬性;二是作為社會人而具有的社會生命(自主的創造性生命),是在人類創造的價值關系當中展開的人類的特有價值。對于所有個體而言,要想實現人權價值,必須經歷從自然生命到社會生命的轉變,從自然價值到人權價值的實現。這是人之為人的價值要求和本質體現。也就是說,人一生下來只是承繼了自然屬性的部分,而人的本質只能在社會屬性中得以展開。“社會”是人類共同體存在的基本形態,是人類實踐活動的主要場域。人權價值就是人類社會要實現的終極價值。要想實現人權價值,就必須通過現實的實踐活動生成人作為存在主體的那個部分。僅依靠具有濃厚自然屬性色彩的人性不足以支撐自然人向社會人轉變的實踐歷程。用人權價值來替代人性對實現人的本質解說,就將人作為獨立于自然界的價值主體確定下來。因此可以說,人類所創造并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也就是獨屬于人的價值形態世界。
二、人權價值德治化的困境
資本主義的人性論旨在從人的德性出發,論證出一套具有普世意義的人性體系,這就把彰顯人性的人權引向了“崇高”道德的深淵。人權能夠閃現人性的光輝,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實。但如果從價值層面來思考人權,就要清楚地認識到人權價值的道德限度,否則就會陷入人權價值的道德泥淖里無法自拔。在道德治理層面,人權價值確實發揮著判斷人性善惡的價值評價功能和作用,這是塑造人的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手段。尤其是在當今社會,針對人們道德感的普遍弱化,社會頻發令人深思的道德事件,不由讓人感到一場道德危機迫在眉睫。市場經濟的發展,信息社會的成長,法治社會的進步,都使民眾越來越重視人權價值的實現問題。然而,民眾對人權價值的實現又存在不合法、不通情、不達理的現象,這是人權價值德治化與法治化、信息化、經濟化不同步發展的表現。當人權價值德治化滯后于社會發展和進步的時候,就會被人為地放大人權價值德治化的缺陷,使之陷入飽受爭議的困境當中。人權價值德治化確實存在與生俱來的不足,其對人性的推崇、對角色的依賴、對崇高的構建,都是其進一步發展需要突破的瓶頸。其一,人權價值德治化的人性困境。人性是與物性、獸性、神性相對應的價值存在。人因具有人性,故從自然界中獨立出來,獲得了實現人權價值的本質屬性。然而,資本主義的人性論即抽象人性論,卻鼓吹抽象的政治人。當現實生活中感性的人被抽掉了豐富的實踐內容,只剩下呆板干癟的政治符號成分,人就會淪為資本主義機器運行的部件,從而被異化為只是物性的工具。這既是資產階級以神性自居而對勞動者的頤指氣使,更是資產階級對勞動者的獸性大爆發。從表面上看,資本主義整個社會在宣揚人性,而在實踐當中,資本主義社會卻整體淪為了物性、獸性和神性輪番轟炸的場所。這就是歌德在《浮世繪》中所描述的資本主義社會虛偽道德的整個圖景。不管是上層社會,還是底層民眾,都在逃避人性。因為在這里,人性是作為抽象的存在與現實生活相對立的。沒有人相信空洞的口號會對解決實際的生活困難有所幫助。人性就在無法與物性、獸性、神性相抗衡的情況下,被邊緣化為一種“善意”的謊言,被愚弄為一種美麗動聽的口號。人權價值不同于人性,但其在社會中也發揮著德治的功能。當民眾為實現人權價值而努力奮斗的時候,人權價值就作為個體與社會的價值維系,將個體的價值要求與社會的發展進步聯系在了一起,實現著二者之間的良性互動。這種價值維系會引領個體的道德認知,提升個體的道德觀念,增強個體的道德能力,從而將個體塑造成為符合社會道德要求的道德主體。當民眾無法滿足正當的人權價值訴求,就不會將它視作調解社會行為的一種重要方式,從而導致人權價值失去道德調解的功能。這兩種把握社會的方式都是個體從人性出發,對人權價值的道德審視。然而這只是人權價值呈現出來的道德面孔,并且民眾是以功利主義的心態來對待這幅面孔的。人性有趨利避害的弱點,當人權價值有利于人的生存時,就會被擺到神壇上予以膜拜,反之,則會棄之不理。這是人權價值德治化面臨的人性困境。無論個體如何對待人權價值,它都為所有人提供了實現人權的價值指引。這是人權價值對人性的超越。其二,人權價值德治化的角色困境。權利總是跟角色聯系在一起。在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當中,個體所處的社會身份或社會角色決定了其所享有的權利和應承擔的義務。這集中體現在中國封建社會的“三綱五常”當中。“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要求,個體處于什么樣的社會地位,就要扮演好相應的角色,也就是要履行與角色相一致的權利和義務,絕不能亂了社會等級秩序。這就是當時社會人權價值的實現方式。儒家非常重視通過德治的方式來實現人權價值。孟子認為全社會踐行三綱就如對“仁義禮智信”的遵循一樣,是發端于人的內心。故而他才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儒家認為,通過“三綱五常”教化民眾,就能使之與禽獸有別。這是因為“三綱五常”賦予人一定的道德角色,使之雖可能有禽獸之舉,卻不能泯滅人之真情。所以孟子發問道:“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孟子•告子上》)從儒家對實現人權價值的思考可以看出,局限于道德角色當中的人,只能在相應的倫理體系里實現有限的人權價值,這是人權價值德治化的角色困境。要想沖破這種角色困境,就要真正認識自身的人權價值。人權價值賦予“人”這個角色以基本的權利內涵和價值意蘊,而不是賦予特定角色下的“某個人”以相應的權利話語和價值表達。這里的“某個人”就是“單向度的人”(馬爾庫塞語)、“被異化的人”(馬克思語)。更進一步而言,角色人無法從整體上對“人”進行全面把握。而人的本質及其展開恰恰是要把“人”作為人類存在的整體予以把握,才能一窺人類為權利而奮斗的完整圖景。論證人權價值的意義恰好在于,要在每一個作為“人”的個體心中樹立其應當享有的基本權利,實現其應當展開的基本價值,這是具體語境下的角色人無法企及的重任。每一個個體都是實現人權價值的角色人,都不能超越歷史局限性的束縛。在實現人權價值的每一個歷史片段中,都閃現著人性的光芒。只有思考形形色色的角色人實現人權價值的不足,將其展開為一幅實現人權價值的壯麗畫卷,才算是對實現人權價值的有益思考。其三,人權價值德治化的崇高困境。當把人權價值作為立足于人本身的價值需要,而構建成需要認真對待的價值體系時,并不是說人權價值就是完美無缺、無懈可擊的。那種把人權價值看成是某種一成不變的真理,予以絕對化對待的行為走向了一個極端的片面。這種認識在倫理學界并不鮮見。琳達•扎戈澤波斯基(LindaZagzebski)就認為,道德典范擁有道德實踐的信條,這是與生俱來的欽佩之情。“挑選符合典范能夠滿足好人的指稱無需借助于描述性定義的使用。”[8](P49)這就是說,典范所具有的“好人的指稱”具有道德上的自足性,無需任何外在描述性的肯定就具有“好人”的道德意義。她對道德典范的理解就如同人權價值被崇高所綁架。人權價值具有非排他的利他性,能在實現自身的過程中映現人性的崇高。特別是道德典范對人權價值的實現,更具有被放大的道德示范效應。這就容易誤導民眾把道德典范泛道德化、神化,迷戀于人權價值的正向道德指引。而當道德典范的偶像形象被打破,民眾又不能順利地實現人權價值時,就會滋生否定一切的虛無主義。人權價值的德治化確實能激發道德典范的崇高道德實踐,也能引導普通民眾建立欽佩、同情、共鳴的道德情感,進而認同道德典范的行為模式。這是把人權價值引向崇高的魅力所在。與此同時也必須看到,人性是復雜的,實現人權價值的過程也是復雜的。僅靠崇高的道德指引,不足以實現作為整體的人權價值。正向的道德承諾并不能有效阻止道德滑坡現象,更無法保證人權價值的充分實現。對于復雜的現實生活而言,實現人權價值面臨著多元價值存在的沖擊。僅靠正向道德典范的神化作用,已不能有效解決社會的道德失范現象。而每一種道德失范都與相應的人權價值缺失有著直接的關聯。如何對待應然的崇高與實然的實踐,就成為實現人權價值必須面對的問題。應然的崇高只有從道德依據的追尋,落地為實現人權價值的實踐,才能為自己找到獲得生命力的根據。這一過程既是用崇高來證實人權價值的過程,又是人權價值的自我證成過程。這也是解決人權價值德治化崇高困境的出路。
三、人權價值德治化的實現路徑
人權價值德治化是從道德教化的路徑出發,對實現人權價值展開的思考。人權價值作為內心的一種價值信念,旨在為人們樹立自覺實現人權價值的道德自律。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讓民眾理解人權價值,及其在實踐當中所展開的道德意蘊和價值。人權價值德治化的實現,就從民眾對人權價值的重新認識展開。
(一)從必需品到搭便車:人權價值的利他性人權價值具有利他性特征,這種利他是非排他性的利他。所有人都有人權價值的需求,都有實現人權價值的欲望。任何一種具體的人權價值,對于任意的“某個人”都具有同樣的價值主張。特定個體實現人權價值的行為,不僅展現了一種自我的價值關懷,同樣是對他人實現相同人權價值的關懷。人權價值在任何一種權利實現、價值追求、實踐方式、敘述表達和展開過程中,都具有非排他的利他性,必須深入到特定的社會語境、歷史背景、時代精神和具體實踐中考察人權價值的利他性,才能破除資本主義人性論的抽象性、口號式的價值表達。這是馬克思主義者在現實生活中,從具體的、歷史的、實踐的人出發,實現人權價值的唯物依據和科學方法。所有人對人權價值的需要如同對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必需品是民眾日常生活當中須臾不可或缺的存在。民眾在衣食住行當中所享受的權利、所實現的價值就是人權價值。可以試想一下,誰要是離開健康的空氣、飲水、食物,乃至必需的醫療、教育、交通等服務設施,能像其他人一樣正常生活,那會是一種何等不可思議的場景。即使是丹尼爾•笛福的小說《魯賓遜漂流記》的主人公,也需要運用人類的工具,按照人類的生活方式為自己開辟實現人權價值的新道路。人權價值是人類的“必需品”,就決定了誰都可以搭人權價值的“便車”。搭便車是一種無需支付任何成本卻能享受收益的行為。人權價值是人類為實現基本的生存和發展而創造出來的一系列權利價值。這種權利價值的基礎性就決定了每個作為主體的“人”都可以主張人權價值。在貧富分化嚴重、權利義務分配不均、社會等級格局明顯的社會里,搭人權價值便車的主張更具有現實意義。尤其是對窮人而言,人權價值的邊際效用(MarginalUtility)比富人大得多。福利經濟學認為,同樣單位的貨幣對于窮人和富人所帶來的福利是不一樣的。在窮人眼里,為數不多的貨幣就能給他們帶來極大的幸福感和滿足感。可這些貨幣未必能給富人帶來同樣的價值感受。人權價值就像這些貨幣,在掌握權力、資源和財富的人那里,沒有比在需要人權價值的窮人那里帶來的邊際效應大。可事實上,人權價值是誰都可以搭便車的必需品。這種利他性要求人權價值在所有人身上都能得到公正的實現,這是人權價值德治化的現實要求。由此可見,社會只有解決不斷分化的利益矛盾問題,才能逐步實現人權價值的利他主張。
(二)從人權福利到人權象征:人權價值的幸福感實現人權價值有利于解決民眾的幸福感問題,這可以通過人權價值在窮人身上的邊際效用來說明。人性有自私的一面,之所以不能通過人性治國,是因為掌握社會財富的少數人一般不會將手中的財富用于社會公共事業,而財富在窮富之間的分配對實現人權價值起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以1單位的貨幣為例,一塊錢在富人手里可能不會給他增加太多的幸福感,可是對于已經失業的窮人、饑腸轆轆的乞丐、債臺高筑的破產者而言,一塊錢就是眼下的溫暖、肚皮的福音、生活的希望。一塊錢給后者帶來的幸福感比前者要多出很多倍,這是因為一塊錢對于后者而言就是人權價值的實現,而在前者看來可能什么也帶不來。在制定社會公共政策時,如果社會總財富(無數個一塊錢)向窮人傾斜,即使社會總財富沒有增加,社會的總體福利和民眾的總體幸福感也會得到極大地提升,直接對人權價值的總體實現產生不可估量的重要影響,這就是增加社會福利對實現人權價值帶來的正向促進作用。從這一視角而言,社會福利可以說就是人權福利。提升社會福利不僅能增加踐行人權價值的幸福感,而且有利于打破因社會角色固化而對實現人權價值造成的藩籬。社會角色往往決定著社會優勢資源的分配和享有,實現人權價值與掌握社會資源往往呈正相關關系。普遍提升社會福利,就使社會資源在不同社會角色之間產生了流動,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因社會角色固化而產生的社會矛盾沖突問題。這既是實現人權價值的物質性福利,也是實現人權價值的價值表征。對社會底層民眾,尤其是窮人而言,社會福利不僅是一種人權福利,更是一種人權象征。國家在醫療、教育、住房、交通、通訊等涉公服務領域的福利性政策,正是在逐漸解決民眾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問題。毫無疑問,這正是當今中國最需要解決的人權問題。人權價值在上述領域的實現,不僅是社會福利的普及,更是國家對人權符號的重視結果。人權價值的象征意義就實現于人權問題的不斷解決過程之中。當然有一種聲音認為,增加社會福利會助長社會中的“懶漢”。事實上,所謂的“懶漢”是社會為最需要幫助的人所貼的道德標簽。在當下中國,接受福利救助的大多是社會底層民眾中的老幼病弱殘群體,他們所享受的福利不是“發達型福利”,而是解決基本溫飽問題的“發展型福利”[9]。而社會中的青壯年基本上被制度排除在享受福利的群體之外,這就決定了我國的社會福利還是以解決人權問題、實現人權價值為主。
(三)從內在價值到內在品德:人權價值的德治化人權價值是人的內在價值,人對自身內在價值的擁有經歷了一個不斷生成的過程。人一開始是借助神話來擺脫動物性,借此擁有自身價值。在神話階段,宗教中的救世主是人類實現內在價值的主要寄托,尤其是上帝的形象,為人類擁有內在價值提供了根本依據,這種認識一直從西方文明延綿至今。在哲學階段,人類能對自身的內在價值進行獨立反思,這是人類把握生活世界的又一方式。借助價值邏輯,人類審視經驗事實對生活世界的意義。生命價值、人生價值、終極價值等研究,促使價值哲學成為人的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在科學階段,人類運用實證研究探索內在價值的奧秘,這是科學從哲學中成功分娩出來的標志。人類運用科學把握客觀規律,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內在價值。直到現在,人類依然主要通過宗教、哲學和科學來把握人的內在價值。只不過“在今天通過反省自我、透視自我,在前人認識的基礎上去重新理解自我,達到比前人更接近于人作為人的真正本性的認識,也就是克服抽象人性觀點、對人性形成具體的看法,是具備了更充分條件的。”[10]人權價值從內在價值到內在品德的轉換,是人權價值德治化的主要表現形式。作為“人”的一員,個體都擁有尊嚴、平等、自由等內在價值,這種內在價值在現實生活中會內化為人的行為品德,成為其參與社會關系的無形保障。人類因為有無形的品德保障,才能構建出一套倫理化的社會關系,從德治化路徑展開了實現人權價值的探索。人權價值具有非排他的利他性,對所有人而言都普遍適用。那為什么人權價值在個體身上有不同程度的實現呢?因為個體的內在品德不一樣,對人權價值的理解不一樣,實現人權價值的實踐就不一樣,實現的結果也就千差萬別了。在個體身上,人權價值從內在價值向內在品德的轉換,也就是人權價值從應然狀態向實然狀態的轉型。雖然這種轉型仍然是在倫理道德的層面進行分析,卻使人權價值獲得了具體的道德指稱。個體運用這種道德指稱,就能在具體的情況中,約束觀念想法,規范自身行為。于是在現實生活當中,人權價值的內在品德就使其內在價值獲得了個體經驗上的證實。這樣,人權價值既能在價值層面確證作為“人”而擁有內在價值,又能在倫理層面確證作為“有德性的人”而擁有內在品德,更能在實踐層面確證作為“踐行德性的人”實現人權價值的人性行動。這是人權價值德治化的最終目標。
參考文獻
[1]任帥軍.作為人權價值的“綠色”價值[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4).
[2][4][5][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
[7]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肖巍.社會保障權及其實現要領[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1).
[10]高清海.論人的本性——解脫“抽象人性論”走向“具體人性觀”[J].社會科學戰線,2002,(5).
作者:任帥 單位:軍復旦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