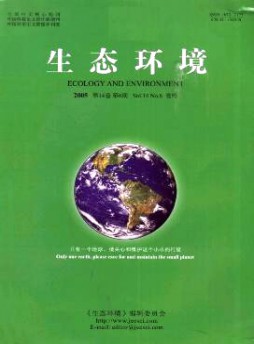生態環境修復的文化差異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生態環境修復的文化差異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廣西民族研究雜志》2014年第三期
一、民族文化差異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在我們居住和生活的地球上,是一個擁有眾多民族的世界。而各民族之間由于自然環境和歷史發展所形成的民族差異和特點,從而導致了每個民族的經濟社會發展與生計方式也呈現出各具特色的狀況,其對所處生態環境的影響也各不相同,因環境而異。在當今的世界上,單一成分的民族國家都較為少見,絕大多數都是多民族國家。如在亞洲,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境內就擁有100個以上的民族;中國、越南、菲律賓擁有50多個民族;緬甸、伊朗和阿富汗也擁有30多個民族。在歐洲,芬蘭、法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英國、西班牙、俄羅斯等都是多民族的國家。在美洲,美國和巴西各有100多個民族;加拿大、墨西哥和阿根廷各有50多個民族;玻利維亞、委內瑞拉、秘魯、哥倫比亞和智利各有20多個民族。在這些多民族國家中,由于各自的自然經濟條件和歷史發展背景不同,無論是不同國家或者是同一國家中的不同民族,其經濟社會發展和生計方式都呈現出不同國家和民族的個性和特點,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也各不相同。印度是亞洲國家中的一個多民族國家之一,現有大小民族300多個,分屬845種不同的語言和方言。在這些眾多的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印度斯坦人(Hindustanis),約有1.8億,占全國人口的28.2%。這一民族主要從事農業生產,其中居住在其國家北部地區的印度斯坦人主要種植小麥、玉米、豆類等,而南部地區的印度斯坦人則以種植水稻、甘蔗、棉花等為主。紡織、刺繡、金屬加工等精湛手工藝是印度斯坦人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手工業。比哈爾人(Bikaris)是印度人口中位居印度斯坦人之后的第二大民族,約有6600萬人,占全國人口的10.3%。比哈爾人主要從事農業和畜牧業生產,農作物以水稻為主,山區靠白薯、高粱和豆類等雜糧作生活中的糧食補充。拉賈斯坦人,雖然這個民族在印度只有1400多萬人口、占全國總人口僅2.2%,但其國內的生計方式有的從事農業生產,也有的從事商業活動、手工業生產等,多數人以玉米和高粱為主食,日常生活則以素食為主。其他一些民族如孟加拉人(Bengalis)、馬拉地人(Marathis)、奧里雅人(iy)、旁遮普人(Panjabis)、阿薩姆人(samese)等,大多從事農業生產,以種植水稻為主,喜食大米、魚蝦等。
印度是一個人口比重較大的國家,現有居民已達10余億人,全國的一半人口主要居住在恒河流域及沿海地帶,這一地域的每平方公里達500~1000人左右,而在北部、西北部和東北部的沙漠地帶與高密山區,每平方公里不到10人。為解決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印度除了大力興建水利設施,進一步擴大灌溉面積外,還積極提高農業生產的現代化水平。具體措施有:一是引進、培育和推廣優良品種,如現在的小麥和水稻的高產品種種植面積已達95%以上。二是大幅度增加化肥的施用量,如在印度的旁遮普邦,1960-1961年度,全邦只施用化肥5000噸;1965-1966年度增加到4.6萬噸;1968-1969年度全邦平均每公頃種植面積施化肥34.4公斤;1973年旁遮普化肥廠生產化肥164.1萬噸,使化肥施用量每公頃增至74.5公斤;1978-1979年度又提高到94.8公斤。三是實行農業機械化,1960-1961年度,旁遮普邦僅擁有拖拉機4935臺;1965-1966年度發展到10636臺;目前全邦共有拖拉機14萬臺,全部谷物的種植已實現機械化。現代化農業的高速發展,就旁遮普邦的生活水平提高而言,的確帶來了諸多的利益,但由于印度國家的政治體制原因,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除了印度的社會制度所帶來的農村兩極分化,廣大貧苦農民負債累累甚至喪失土地等以外,更為嚴重的是生態平衡受到了破壞,影響了農業生產的良性循環,大量施用化肥而造成土壤板結;大量而長期的灌溉從而使地下水飽和,造成土壤鹽堿化;農藥的大量使用又增加了環境的污染等等。[4]300-302這種由社會經濟發展或生計方式而導致的生態環境問題,在其他一些多民族國家中我們還可找到相應的事例。如位于南美洲的巴西對其國內北部地區亞馬孫平原國土的開發,這一舉措所引起的生態環境問題,同樣值得我們反思。亞馬孫平原位于巴西北部,背靠安第斯山,面迎大西洋,亞馬孫水系流貫其間,形成360萬平方公里的沖積平原。由于亞馬孫平原地處赤道低緯帶,大部分地區的海拔在150米以下,終年高溫多雨,熱帶雨林氣候分布廣,生物多樣性的植被發育十分豐富。區內的深林覆蓋率達70%以上,樹種繁多,達4000多種,是世界上最大的熱帶雨林區。對亞馬孫平原的國土開發始于戰后的20世紀40年代中期,70年代才加快步伐,成為國家經濟開發的重點地區。開發亞馬孫地區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在大肆砍伐森林的基礎上實施以下計劃:一是修建公路;二是移民開荒,發展農業;三是開辟牧場,發展養牛業;四是發展工礦業。亞馬孫平原通過上述開發計劃,的確在短期內對當地帶來了一定的社會經濟效益:⑴亞馬孫公路網通過庫亞巴和巴西利亞與國家經濟重心東南部及南部公路網聯成一體,有利于北方經濟開發和對外聯系,并吸引大批移民到新墾區定居,對鞏固北部邊陲有很大的戰略意義。⑵增加了谷物生產,滿足了新遷移民的生活要求。70年代中期的農業移民和墾荒,將土質肥沃的原始森林變成生產水稻的天然糧倉,并取得了顯著成效,使這一地區現已移民6000多戶,開荒30000公頃。⑶政府依靠亞馬孫地區新開墾的馬瑙斯自由貿易區的工業發展及本區內開采的鐵、鋁土、錳、黃金等礦產資源抵償了沉重的外債。⑷對亞馬孫平原中巨大的水能資源和森林資源的開發,為北方經濟的發展及鋼鐵生產提供了重要的能源。
在顯著的社會經濟效益背后,對亞馬孫平原的生態環境也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和不利的影響:第一,砍伐大片森林(900萬公頃),開辟養牛牧場,得不償失。亞馬孫地區氣候濕熱,疫病流行,并不利于牛群的生長繁殖;由于土壤生態的脆弱性,森林砍伐兩三年后,牧場地力便會衰竭,進而導致更多森林的毀滅。在1965-1979年的15年,巴西政府在亞馬孫地區共投資4億美元資助修建了187個牧場,其結果事與愿違,毀掉價值達77億美元的木材,換來的僅是每年2500萬美元的畜產品,這是一個慘痛的教訓。第二,修筑公路的實際經濟效益并不大。一方面,巴西是缺油國,使用耗油量大的汽車公路運輸與當地的鐵路和水路運輸相比,其成本要大得多;另一方面,亞馬孫公路均為土路,這里常年暴雨,一旦路面養護不善,雨季全然不能通車。第三,毀林開荒發展農耕業和畜牧業,并未達到外來人口在農業地定居的目的,那些從干旱區到濕熱區開發農業的移民,遇到了氣候濕熱、病蟲害、草荒、土地開墾后肥力減弱、農作物產量大幅度下降等問題,遠比在原故土解決吃飯問題更困難,在此背景下,到70年代已有30%的東北移民又倒流回鄉。由此可見,亞馬孫地區的農業開發是弊多利少,而預先確定的各項目標基本沒有達到。相反,卻在社會、經濟、生態等方面產生了許多不良的后果。[4]281-285地球作為一個生命體系,它提供給人類社會的生物物種豐富多樣,而生物物種間的依存制約關系也十分復雜。但是,人類社會對自然界提供的資源似乎并不領情,在當今世界上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在直接利用這些生物資源的方式與手段出奇地單一,僅是依靠有限的10多種農作物和20多種家畜家禽,來支撐人類80%以上的生命物質和生物能的供給,而其他的生物資源卻置之不理,甚至視為穢物。如果這不是人類對地球生命體系的無知,就是對地球生命體系的浪費。正是因為人類社會的這種無知與浪費,采取單一的方式去利用地球生命體系的物種多樣性,從而釀成了人類社會與地球生命體系的嚴重對立。
生物多樣性是指生命有機體及其賴以生存的生態綜合體的多樣化和變異性,這包括三個層次———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生態系統與景觀多樣性。在當代,隨著人類社會的演進,與人類相伴度過了數百萬年歷史的生物物種,有的在地球上已經消失了,由于受到人類活動的擠壓,有的種群規模受到擠壓,而植物群落極度萎縮,有的物種甚至處于瀕危境地。與此同時,人類社會馴化的農作物和家畜家禽,其生物特性高度特異化,抗病免疫力也急劇下降,一旦離開了人類社會的撫育就難以存活,有的不得不依賴藥物去維持其正常生產,但這些藥物的使用對人類的身體已經造成了無法預料的傷害。隨著都市化的迅猛推進,對生態環境的人為過度干預,如農田的擴大,工廠礦區的拓展,等等。使得原有生態系統和景觀的多樣性受到了威脅。這給人類的生存環境造成了難以逆轉的生態災變。面對這一嚴峻的形勢,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了《保護生物多樣性公約》,這是人類文化自覺的一種表現,力圖通過對人類行為的規約來實施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用該公約來約束各國的行動,以維護地球生命體系中物種多樣性的延續。但是,事過20余年,我們來檢視該公約執行的成效時,卻令人堪憂,生物多樣性并沒有因為公約的出臺而豐富起來,反而正在減少。關鍵的原因在于,世界各國的國情不同,文化不同,不同國家對待這一公約的反應和采取的行動各不相同,不同國家在其間所獲得的眼前利益不同,有的國家甚至斷然拒絕在公約上簽字。因為生物的多樣性延續靠的是生物間的相互依存與相互制約,這種依存制約關系的復雜性,單靠人力去維持瀕危生物的物種延續無濟于事。因為文化的力量沒有被激發起來,文化的規約仍然被強權霸權所抹殺。這就難怪世界上雖然有這個公約來喚起世人的生態意識,但它的好處卻被不同的文化霸權所分割,因此,若想憑借這一紙公約去解決人類利用資源的局限性與多樣性的矛盾,顯然不是什么良方解藥。
二、多民族國家生態環境修復的差異性
對于生態環境的修復,世界上各個不同的國家從自身的國情出發制定了相應的政策措施,本文分別就美國、澳大利亞、印度等國家以不同方式開展生態修復的舉措,進而深化對這一研究思路的理解。美國不僅是一個移民國家,而且還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在美國的現代居民中有100多個民族成份,其分別由三個部分組成,即美利堅人、未被同化的移民集團和原來的土著人。由于美國的民族眾多、土地的權屬關系十分復雜,對生態環境的修復方式則具有明顯的“美國模式”特色。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就已經啟動了生態系統管理的相關項目,目的在于對那些已經或即將受損的生態系統加以修復。如在公共荒原區協會的資助下,美國密歇根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院的雅妃教授領導的研究小組對美國的生態系統管理項目進行調查和研究,編制出美國有關生態系統活動的詳細名錄,試圖為美國農業部森林局、國家公園局、土地管理局等公共機構提供信息,使之更好地實行生態系統管理,對所轄土地的管理應充分考慮到生態修復的時間和空間尺度,同時也為面臨當地環境挑戰的個人、組織、機構或企業在從各地生態系統管理中借鑒一些寶貴的經驗。項目的目標依次為保護或保持生態系統、修復生態系統、取得利益相關者的支持、維持或改善區域經濟、提出生態系統管理指導方針等。為了保證管理措施對生態系統的修復具有預期效果,充分調動各種各樣的土地所有者參與設計和實施項目活動,從而促進與生態系統功能和結構相協調的人類土地利用,包括采用創新式農業技術、減少土壤侵蝕戰略、木材管理系統的知識等等。[5]印度不僅是南亞最大的國家,而且也是世界上森林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但由于這里的各民族長期以來對森林資源的過度利用,致使森林資源迅速減少,并出現了林地退化和水土流失等現象。為了推動森林的管理和生態的修復,1991年6月1日,印度政府公布了發展聯合森林經營的框架,針對國有退化林地確定以利益共享為基礎的聯合森林經營機制,其主要目的是通過森林的保護和修復來確保環境的穩定和維持生態平衡,同時又能提供小型林產品以滿足鄉村中各族人民對少量木材的需求。在印度的憲法中,保護環境被奉為神圣職責,并將其確定為國家及全體公民的責任。在生態修復與保護的方式上,印度目前以三種社會林業的形式來加以實現:一是鄉村片林,即在鄉村公有土地上生產村民所需要的林產品。二是聯合森林經營,即指當地各族人民參與國有退化林地的修復活動,并借此以現有森林來滿足鄉村居民的需求。三是生態開發,即通過開展其它開發活動來提高當地居民的經濟地位,以此削弱其對森林的依賴性。
[6]澳大利亞也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這里的生態獨特、生物多樣性豐富。但隨著城市化速度的加快與程度加深,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國內經濟增長很快,農業、制造業、能源生產、礦業和運輸業對自然資源利用的持續擴大,以致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的壓力,這一嚴峻趨勢促使國家新的生態環境政策紛紛出臺,而參與決策的政府部門、企業、個人和社會團體也采取了相應的行動措施。為了將更廣泛的可持續性戰略步驟轉化成對自然資源的有效管理,澳大利亞采取如下具體的方式:第一,為了遏制威脅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的消極勢頭,已經通過加大現有計劃的步伐,以及推行新的創新機制來保護已經劃定為各類保護區內外的生物多樣性,同時結合聯邦、州和領地及當地政府的工作,限制農業、制造業、能源生產、礦業和運輸業等行業對自然資源的過度利用,以緩解生態環境的壓力。第二,進一步劃清各類保護區內外的動植物棲息地范圍和充分調查保護區內物種群體數量,將其目標量化,強化措施與目標管理成效。如在實施保護的過程中,充分考慮到擴大資金的來源渠道,包括采取對收購和保護協定投資等多種方式,從經費上全面落實對保護區的實際性管理。其具體工作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一是從生物多樣性管理的基礎知識上,開展對保護系統的編目、檢測和開發工作;二是將生物多樣性目標滲透到非保護區土地(如租賃土地和自由保有土地)的管理中,使得保護區域與非保護區域形成對接,與非保護區的民眾之間確立保護權、契約和管理協議等,以實現整體性的保護。三是與所在地民眾密切合作,以立法的形式將屬于當地人所有和管理的14%的領土納入到生物保護計劃,分明權責利;四是將保護區內的農業、林業和漁業活動的目標具體化,以使可持續利用,讓當地人從中獲得實惠,而積極參與到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環境保護的行列中來,把保護生態環境當做自己的使命。第三,在具體的環境修復手段上,澳大利亞對生態系統進行管理的有效措施有:一是加強生態環境政策的效力;二是在經濟決策中考慮到生態環境;三是實施生態可持續發展戰略;四是在礦業中納入生態環境方面的考慮。此外,還對生態系統管理方面進行了立法,制定了相關的法律法規,如制定了《環境保護和生物多樣性保護法》、《水資源法》、《土壤保持和土地保護法》、《牧場管理和保護法》、《林業法》、《漁業法》、《國家防火法》、《動植物防治法》、《本地植被法》、《荒地保護法》、《國家公園和野生動植物法》等。[7]以上這些舉措對這些國家所處生態環境的修復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維護了這些國家生態環境的安全,但也呈現出不同國家民族文化的差異性。這種具有文化差異性的生態環境修復措施,給其他多民族國家的生態修復提供了可資參考的借鑒。
三、特定文化下的生態修復
我們認為,生態修復是一個極為抽象的理想目標,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如果不能將這一目標具體化,生態修復也就沒有了特定的對象,這樣的生態修復就不具有任何實際意義。因此,在實施生態修復時,必然需要將其具體化。在當今的地球上,人類是靠文化的分野而存在,不同文化下的民族對生態安全的理解不盡相同,對生態資源的要求與利用也不盡一致。因此,可能采取的生態維護與生態修復的措施也互有差別。可以說,任何具體的生態修復,都具有明確的文化內涵。如果忽略了文化的存在,具體的生態修復就無從談起,也就是說,生態修復乃是特定文化的產物。當代人類所面對的生態危機,是人類不同文化對其所處環境持續作用的結果,也是其文化長期偏離其環境累加起來而釀成的災禍。從這一點來說,特定的生態失衡,那是特定文化的失衡。因此,如果不能對生態失衡乃至生態災變的所屬文化展開討論,那么,其生態災變所引發的后果究竟應當由哪些民族承擔責任,各自承擔什么樣的責任,均無法具體認定。目前,人類社會關注的頭等生態問題,就是全球氣候變暖,以及由此導致的海平面上升和溫帶草原的日趨干旱。生態學家通過他們慣用的研究方法得出結論,認為全球氣候變暖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過大導致的結果。但是,我們需要追問的是,這個責任應該由誰來負呢?是誰在排放過量的二氧化碳,這樣的事實至今無法裁定。即使有些機構勉強做出了裁定,因為霸權話語的存在,這樣的裁定無法讓相關的民族心服口服。我們知道,當今生存在地球上的所有民族幾乎都是靠燃燒生物能源獲取熱能,不論是石化能源的直接使用者,還是在其消費中的受益者,無不在排放二氧化碳。有了這樣的資料,以至于那些認定機構由此做出裁定,由二氧化碳排放引起的全球氣候變暖、生態失衡,地球上的每個民族都有責任,都應該來承擔這份責任。
但是,從生態人類學的視角出發,做進一步分析,我們就會發現,其實在地球上的各民族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可同日而語,其差異大得驚人。可以說,西方工業民族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大超過非洲狩獵采集民族的數百倍,甚至上千倍。如果不能將這樣的差異事實進行說明,而認為所有的民族都排放二氧化碳,因而均擔其所造成的生態失衡責任,顯然有失公道。就是今天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國家美國至今仍未在“京都議定書”中簽字,一直以自身利益為理由拒絕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而不愿意承擔起相應責任。這樣的爭議,在國際大會上多次被提出討論,但美國至今依然唯我獨尊,我行我素,不愿意放棄從中獲得的好處。我們知道,全人類要形成這樣的共識,人類以文化分野為民族差異這一客觀存在一直在困擾著人們的思維,在西方話語霸權下,以所謂的“人權”為幌子來抹殺人類文化事實體系的差異性,進而宣稱生態失衡生態災變的后果需要人人均擔其責。但是,生態人類學告訴我們,在地球上復雜的生態系統中,各民族的文化運作僅是其中的一個有限部分,并且各種文化參與運行的內容和方式互有區別。如果這樣的基本事實得不到確立,這就必然導致不同文化在圍繞溫室氣體排放這一具體項目上的責任關系無法理順。在這樣復雜的背景下,要達成共識,有點望梅止渴之感。世界各民族無不是圍繞著對自然資源的消費而獲得延續與發展,并且在對資源的利用過程中還存在著相互的牽連性。就以化石能源的消費為例,不僅大量使用化石能源的民族獲得了發展的機會與空間,而且那些產出化石能源并出售的民族也在從中獲利。當然這里也存在一個獲利是否合理的問題,但無論如何,產出石油的民族也不能說在二氧化碳氣體的排放上毫無責任。此外,發達民族通過對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費所生產的產品,通過市場擴散到其他民族中,其他民族也分享到了這種產品的便利,那么這些從表面上沒有與化石能源有直接關系的民族需不需要承擔間接的責任等等,這樣的問題,至今仍然沒有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案,仍然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總之,就全球化石能源消耗對環境所負責任來說,其責任不均,責任大小、直接責任、間接責任等難以厘清。在討論各民族面對同一內容的生態失衡時,應該如何分擔責任,則是一個十分艱難的事。當代面對生態失衡的另一個熱門話題,就是全球森林面積萎縮的問題。我們知道,推動森林擴大肯定具有生態效益,但其所形成的生態效益卻無法在各民族間均等分享。諸如對于處在江河上游的民族而言,森林面積擴大意味著上游居民的牧場和農田要壓縮,一旦壓縮了牧場和農田,其正常的生計就會受到影響,其生活質量就會下降。
這樣的事實,在我國也十分突出,以長江流域的生態維護為例,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說明。長江發源于青藏高原,流經地區的民族有藏族、羌族、彝族、普米族、納西族、傈僳族、拉祜族、苗族、仡佬族、土家族等民族地區,這些民族的傳統生計資源主要依靠森林與草原。但為了保護長江中下游的生態環境,需要生活在上游的這些民族實現“天保林工程”———退耕還林、退耕還草。這樣一來,上游諸多民族的傳統生計方式不僅沒有獲得升級換代的機會,反而要實現生計轉向,這對于一個民族來說不是一個說轉就轉的事,整套的生計策略都需要全面改造,這不是短時間就能夠實現的事。但在國家主導下,一紙文件就需要執行,需要立即行動來實現對長江中下游生態環境的維護。這樣的生態維護行動對下游的民眾來說無疑是一件特大喜事,但對上游諸民族的民眾來說也是一場嚴峻考驗,這其間的利益至今仍然沒有獲得很好的配置。我們知道,森林面積擴大后,特定區域的生物多樣性水平無疑得以提高,由此也會帶來巨大的生態效益。但在這樣巨大的生態效益配置面前,不同的民族同樣無法均等分享。比如說,那些從事狩獵采集的民族可以從森林面積擴大中獲得更多的采集和狩獵對象;但對農耕民族而言,其農田耕作面積就會減少,原來富足的生活就會受到影響,而且隨著森林面積的擴大,農田莊稼作物遭受野生動物侵擾的風險也會更大,因此會安排更多的勞力來預防野生動物對莊稼的破壞,從而加重了其勞動負擔。因此,森林擴大對原住地的農民來說,很難直接從中獲得效益。在退耕還林的過程中需考慮這些因素,如果不做出補償,森林面積擴大與農田面積縮小的矛盾,就會引發為民族間的沖突。總之,泛化的生態修復只是一個總目標,這樣的修復目標落實到具體民族,情況便千差萬別了。不同的民族在分享其生態修復的效益時不具有均等性。因此,對每一項生態修復指標,不同文化規約下的各民族做出不同的反應。這種非均衡性早已被相關民族的文化所規約,其生態修復所呈現的效益只能在特定民族文化的“弧”內延展開去,實現其價值。[11]56如果拋開民族文化的差異,僅僅按資源的自然屬性以平均數在民族間均衡配置,不僅會受到相關民族的文化抵觸,也會使生態修復的效益下降,甚至使這樣的再配置根本無法實施。可見,生態修復是一個文化概念,而不是一個抽象的全人類共同利益理念,最多只是一個理想的目標而已。這就使得我們在開展生態修復時,勢必從具體文化出發,才能將其目標實現。
作者:羅康隆單位:吉首大學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