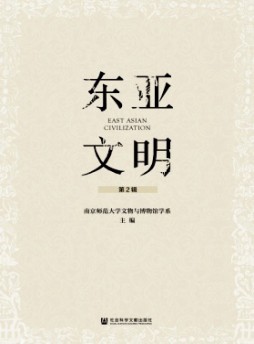東亞經濟增長爭論探討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東亞經濟增長爭論探討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1·世界銀行報告的基本結論
克魯格曼對于東亞經濟增長模式的批判,源于世界銀行1993年出版的一本著名報告《東亞的奇跡:經濟增長和公共政策》(TheEastAsianMiracle:EconomicGrowthandPublicPolicy,WorldBankPolicyResearchReports,1993)。世界銀行的這本報告試圖分析并總結東亞4個新興工業化經濟體(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經濟增長的經驗,并希望通過總結這些經驗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指出道路。
世界銀行報告的主要結論如下:
a.堅持宏觀管理的重要性,包括穩定的商業環境,低通貨膨脹,有利于鼓勵固定資產投資;謹慎的財政措施,輔之以其他措施保證經濟增長中的公平共享與高經濟增長的成果;有利于出口競爭性的匯率政策;金融發展和逐步的自由化保證國內儲蓄的最大化,推進資源的有效分配,以及與全球金融系統的融合;盡可能減少價格扭曲;采取措施推進初等教育,創立不同技能的勞動力結構,以利于外向經濟的發展。
b.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管理體系,保證長期發展意愿的實現,追求產出與就業的快速增長;政府與工商業之間的互動,同時政府要在工商業者之間創造競爭的環境。
c.政府需要采取積極的政策加快工業化的步伐,增加出口中的工業產品份額;外向發展政策加上匯率政策,就成為達到外部平衡,產生加速GDP增長的需求,促使生產吸收技術,保持國際競爭力的手段。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東亞政府有選擇地選取了關稅保護和鼓勵出口的政策,其中不乏道義規勸、補貼和金融手段,使得實業界可以獲得低成本的融資。
d.政府清楚地表明了可以獲得政府支持的條件,方法是實用的,手段可以靈活使用,在目標不能完成的時候將廢止使用。
2·克魯格曼的批評
按照哥倫比亞大學著名國際經濟學教授Bhagwati(1996)在Cornell大學的一個演講的回顧,在克魯格曼之前耶魯大學的T.N.Srinivasan教授就對世界銀行的研究加以批評,他的理由和克魯格曼的批評一致,認為在四小龍的經濟快速增長中沒有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因此也就沒有技術進步的作用或效率的改善。東亞經濟的重要推動力是資本的積累,資本投入可以解釋經濟增長的80%,因此沒有所謂的東亞經濟奇跡。引起國際輿論界高度關注的則是克魯格曼1994年在《外交》雜志(ForeignAffairs,1994)上發表的一篇題為《亞洲奇跡的神話》(MythofAsia’sMiracle)的文章。克魯格曼對東亞增長模式的批評主要依靠了Kim和Lau的研究(1994)及Young(1992,1994)的實證研究,因此,我們稱之為Krugman-Kim-Lau-Young批評。克魯格曼認為:美國經濟的增長主要來源于全要素生產率,前蘇聯的經濟增長則主要靠要素投入的增加,前蘇聯的增長方式不能持久,導致最后的崩潰;而東亞經濟的增長基本上也是靠要素投入的增加,因此,他認為東亞經濟的增長也是不能持續的,是紙老虎。后來東亞金融危機的出現,使他的觀點大為盛行。
3·一些經濟學家對克魯格曼批評的批評
其實克魯格曼的批評并沒有得到國際學術界的普遍接受,他的文章發表后,國際學術界就有一些系統的批判,但未為國內學術界和媒體所關注。下面主要介紹3篇對克魯格曼文章的系統批評。第一篇文章是前面提到的哥倫比亞大學的Bhagwati,他1996年5月3日在Cornell大學的一個講座中全面批評了克魯格曼的觀點,其主要結論如下:
a·首先東亞經濟奇跡是現實的存在,而不是如克魯格曼所說的神話,東亞奇跡的主要表現就是私營部門投資增長得如此之快,這是其他國家歷史上難以比擬的;
b·這樣一種基本面的突出特征產生的重要原因是這些國家所采用的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
c·大量出口收入的增長可以有能力大量進口含有新技術的資本設備,這樣在快速增長的投資中能夠含有越來越多的技術進步的成分。這一結果導致了雙重的收益,一方面是出口推動的投資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是進口中所包含的技術進步所產生的收益;
d·由于東亞這些國家或地區的較高程度的識字率和教育水平,新一代資本品的社會貢獻大大高于相應的國際成本,因此進一步強化了進口中所包含的技術進步所產生的收益;
e·外商直接投資(FDI)與貿易一樣具有較高的生產率,反映了出口導向發展戰略的成功,而進口替代戰略的不成功則是由于既不能吸引較多的外商直接投資,也不能從這些投資中獲得較高的回報;
f·人們所關注的“產業政策”與東亞經濟的增長關系并不大,甚至有負面的影響;
g·東亞經濟增長模式已經在一些其他國家得到應用并且獲得了很好的后果;
h·他特別指出克魯格曼把前蘇聯與東亞相比較是錯誤的,前蘇聯的增長依靠公共儲蓄與投資,而東亞依靠的是私人儲蓄和投資,在吸收外國技術方面也不同,因此亞洲經濟的增長與前蘇聯不同,是可以持久的。
第二篇文章由現任香港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EdwardK.Y.Chen,1997)寫成。陳坤耀原任香港大學教授,是國際學術界最早研究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的學者,他對克魯格曼文章的批評更多集中于克魯格曼的文章對全要素生產率的誤解,陳坤耀的文章包括了一些偏重技術層面的分析,也更多觸及了克魯格曼的文章在經濟學理論方法方面的缺陷。陳坤耀對克魯格曼文章的主要批評可以概括如下:
a·在經濟增長的核算中,作為技術進步代表變量的全要素生產率是核算中的殘差,因此,很大程度上決定于投入要素的數據是如何測定的;
b·關于東亞經濟奇跡的爭論,與所用的數據有關,也與相應的定義和概念有關,他認為克魯格曼、Young和許多參與這場爭論的人并沒有很好地了解全要素生產率研究的理論與實證的發展,在一些基本概念上出現了錯誤;
c·陳坤耀論文的最重要貢獻是清楚地區分了技術進步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區別。他指出:在實證研究中,一些人習慣用全要素生產率代表技術進步,這實際上是一個誤解。所謂技術進步包括與資本融合在一起的(embodied)和不包括資本投入的(disembodied)兩類。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所測定的僅是不包括資本投入的技術進步。因此如果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比較低,只說明不包括資本投入的技術進步比較低,而與資本融合在一起的技術進步仍然是存在的。更準確的表述是,全要素生產率所體現的技術進步是不包括資本投入的(disembodied)、Hicks中性的(Hicks-neutral)技術進步。而在一般場合人們所談論的技術進步的范圍要大得多。在這個意義上,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不等于技術進步,而且,取得不包括資本投入的技術進步并非沒有成本。基于這些,他認為克魯格曼對東亞經濟增長模式的批評是一個誤導。
第三篇文章是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報告(Felipe,1997),在這篇研究報告中,作者對亞洲地區有關全要素生產率的實證研究做了系統、深入的評述和分析。作者在分析方法層面的討論是比較深入的,所指出的許多問題與上面所介紹的陳坤耀的論文的分析比較接近,在此不再贅述。但Felipe的分析走得更遠,他幾乎懷疑在目前這樣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分析框架內能夠正確地理解亞洲經濟發展過程的實際意義。
在此特別需要提到中國學者鄭玉歆的文章(1998),這篇文章發表的時間比較早,但對克魯格曼文章的主要問題都涉及了,例如文章正確地指出了由于方法不同、數據不同而可能導致全要素生產率的不同估計,因此直接在國家之間比較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所可能產生的誤差。該文章還指出了在分析中生產函數設定不同的重要性,以及對技術進步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概念上所已經出現的混亂。鄭玉歆的文章對克魯格曼的文章及相關文章中在有關全要素生產率的計量方法中所存在的問題做了十分深入的分析和批評。該文章還正確地指出了“要素投入作為增長來源的相對重要性是隨時間變化的,是和經濟發展階段以及和要素的性質密切相關的。”十分可惜這樣一篇指出克魯格曼的文章中的基本問題,并加以深入分析的論文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也沒有能夠阻礙一些人繼續宣傳與此有關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
4·國際學術界對這場爭論的回顧與重新檢討
在21世紀的開始,經濟學家們對東亞奇跡的爭論重新產生了興趣,并從一個新的歷史角度對當年的東亞奇跡的爭論再次做了回顧與審視。2001年世界銀行出版了一本新書《從奇跡到危機再到復蘇:東亞四十年的經驗教訓》(FromMiracletoCrisistoRecovery:LessonfromFourDecadesofEastAsianExperience),這本由Stiglitz和Yusuf主編的論文集從歷史的角度對有關東亞經濟奇跡的爭論做了深入的分析,實際上對這場爭論做了總結。其中Stiglitz所撰寫的第13章“重新考慮東亞奇跡”(RethinkingTheEastAsianMiracle)對上述克魯格曼的批評做了回應,他對生產率計算結果的穩健性一直存在懷疑,并提出以下觀點:
a·曾經有研究證明,只要將人力資本的計量方法稍加改變,就會大大改變全要素生產率的計算結果,因此全要素生產率計算的結果與所采用的方法和數據關系很大。由于結果的變異較大,因此展開立論就比較缺乏基礎;
b·如何將資本加以匯總的理論與方法上的困難更是盡人皆知,這一問題在最新研究中雖然有比較大的進展,但仍然可能有較大的不確定性;
c·計算全要素生產率的方法是標準的Solow殘差法,這個方法的假設是生產要素的報酬等于其邊際產出,這只有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中才可能,而亞洲國家的市場顯然不是完全競爭的市場。因此,Stiglitz教授對上述Krugman-Kim-Lau-Young批評中所涉及的全要素生產率計算提出了質疑,同時對這些論文中對全要素生產率計算結果的解釋也提出了質疑。他認為某種意義上,關于全要素生產率的爭論實際是無事忙。
在同一文集中的另一篇文章(Pack,2001)也從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角度分析了關于東亞經濟奇跡的爭論。該研究認為在過去的幾十年,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積累了大量的資本和技術勞動力,并且十分有效地在生產活動中使用這些資本和勞動。許多研究都證明,這些經濟體中的大量企業十分成功地吸收了國際上的技術和知識,這些技術和知識可能體現在設備中,也可能體現在中間投入中,也可能是一種不包括資本投入(disembodied)的技術和知識。而在這些經濟體中都存在一些強大的工業基地,在這些基地中,有現代化的設備,良好的組織,強大的營銷能力,大量的高效率的工人和靈活應付外部沖擊的能力。
而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以上這些成就都被人們所忘記,流行的觀點是衰退不可避免,而政府和企業都不再具有競爭力。但亞洲金融危機之后這些經濟體經濟的迅速復蘇,再次證明上述所獲得的成就還是存在的,并在繼續發生作用。包括在最近的有關全球經濟不平衡的討論中,曾有人指出過去幾年,一個重要的調整已經發生,即一些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工業化經濟(大多數在亞洲)都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已經從國際資本市場上的債務國(地區)變成了債權國(地區)。這些現象的出現未嘗不表明當年對一些東亞經濟的悲觀論斷是站不住腳的。
臺灣經濟學家梁啟源教授最近也根據他本人參與的“亞洲太平洋多個經濟體生產率國際比較項目”(KLEMS)中有關臺灣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對Krugman-Kim-Lau-Young的批評重新作了考察(Lian,2002)。他討論了Young的研究在方法論上存在的問題,并加以改進,結果發現認為臺灣的經濟增長不存在技術進步的批評是不成立。
二、我們對克魯格曼批評的分析與評價
在這一節我們力圖全面討論克魯格曼批評,有些評論與前面提到的學者的批評相似,為了相對完整,我們也再次做了闡述。
1·關于全要素生產率計算方法的發展歷史及其意義
全要素生產率測量是近50年來經濟理論和實證研究的一個焦點領域,研究目的是想在數量上確定不同投入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單要素生產率如勞動生產率和資本生產率只考慮一種要素的投入,而全要素生產率考慮的是所有的投入要素(勞動、資本等),因此在分析上要優于單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核算理論中全要素生產率是一個“殘差”,等于產出增長率與各個被計算到的投入要素增長率加權和之差。
為了解釋我們的觀點,需要回顧一下全要素生產率計算方法的歷史,該歷史可以分成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為Solow以前時期,最早提到生產率概念的是Copeland(1937),以及Copeland和Martin(1938)。最早實際估計這個變量的是Stigler(1947),Stigler在其1947年的研究中已獨立地提出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概念與分析方法。最早將生產函數方法與生產率聯系在一起的是Tinbergen(1942)。總量生產函數的起源是所謂Cobb-Douglas生產函數,這一模型最初的目的是揭示生產中的規律并希望利用經濟數據來驗證這些生產中的理論模型。Tinbergen首先把這一生產函數用于研究經濟增長問題,他在模型中增添了一個時間趨勢,并用這一項來表示效率,也就是生產率的概念。第二個時期為Solow1957年文章到Jorgenson和Griliches1967年文章之間。首先將生產函數與指數方法的理論聯系表述出來的是Solow(1957)。Solow在1957年那篇文章,提出了一個計算全要素生產率的方法,但認為美國的經濟增長80%來自于全要素增長率,也就是技術進步的實證結論并沒有得到后人的贊同。現在討論美國經濟的全要素增長率問題,通常強調的是Solow的理論貢獻,很少提他的經驗結論。在此期間研究美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以Kendrick和Denison為代表。這些人的實證分析結論,跟Solow當年是不一樣的。
第三個時期為Jorgenson和Griliches1967年文章之后。該文章批評了Denison等人的工作,認為他們在投入的計量上存在誤差,因而高估了經濟增長中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他們的論文認為從理論上分析,所謂的全要素生產率實際上是一種計算上的誤差,這個誤差來自于對投入要素衡量的不準確或是某些對生產有貢獻的要素沒有被包括在生產函數中所致,如果把各種投入要素都包括在內并準確衡量則這個誤差不存在,全要素生產率就為零。因此,當發現一個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高,很可能只代表對這個國家的投入要素的衡量不準確或是某些投入要素未被包括在內。同時,也意味著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必須對投入要素有準確的衡量,并且,跨國的研究應該采用一致的測算方法才有可比性。
目前國際學術界的大量研究所依據的全要素生產率的計算方法是根據以上所提到的建立在第三時期所發展的方法。這一點的最重要的標志就是OECD所出版的關于資本估計的手冊(OECD,1999)和關于生產率估計的手冊(OECD,2001)。該方法仍然保留著完全競爭市場和規模收益不變的假設。對于該核算方法的上述基本假設可能不滿足的問題也早已被人們所認識,之所以沒有發展出新的核算方法,就在于在如此復雜、成熟的體系中改變一些基本假設并不是很容易,需要考慮太多因素,同時還需要滿足已有體系的許多要求,這方面的努力一直還沒有獲得成果。而對于全要素生產率核算的基礎理論———生產者行為理論的挑戰,特別是對于生產者理論中的利潤最大化目標函數的假設的研究也很多,如銷售最大化(Baumol,1967),還有管理效用最大化(Williamson,1964)和利潤滿意(Simon,1959)等。但是,微觀經濟學的廠商理論是一個完整的體系,試圖按照其他的目標函數來建立系統的廠商理論的研究,并對微觀經濟學的廠商理論給出完整的替代體系似乎還沒有真正成熟。
目前通用的估計全要素生產率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增長核算方法,其理論模型簡潔,來自于新古典增長理論,是一種非參數的實證估計方法,計算方法主要依靠統計性質與經濟學性質很好的一些指數公式。另一種是經濟計量學方法,一般將總產出或增加值作為因變量,將不同的投入變量作為自變量,通過參數估計的方法來研究。經濟計量學方法測算全要素生產率雖然可以放松增長核算方法中完全競爭市場和規模收益不變等假設,但必須對估計的參數給出先驗假設,并且受樣本觀察值數量的限制,容易出現參數估計不穩定等統計上的問題。而非參數方法將指數方法與生產函數相聯系,更適合于定期的生產率統計研究。OECD(2001)生產率手冊推薦使用增長核算的方法來估計全要素生產率,這也是目前采用最廣泛的測量全要素生產率的方法。美國勞工統計局(BLS)從1983年開始公布的美國全要素生產率,就是用增長核算方法來估計的。
現在有些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直接應用回歸分析方法(例如最小二乘方法)來估計一個帶時間趨勢項的生產函數,這種研究在方法論上是有問題的。原因是:以經濟計量方法來估計全要素生產率的基礎是生產函數的經濟計量估計,而生產函數的計量估計并不是一個單方程的簡單回歸分析的問題,而是包括生產要素需求的聯立方程體系的估計問題,這一點在國內許多關于生產函數估計和全要素生產率估計的研究中都沒有得到正確的理解和運用。即使是C-D生產函數的估計也不是簡單的回歸分析,至少有4種以上基于聯立方程體系估計的估計方法。關于生產函數的經濟計量估計可以參考李子奈的《計量經濟學———方法和應用》和任若恩的《計量經濟方法論———關于在中國應用的研究》。而在英文的文獻中,則有大量的研究,如最早的經典文獻Marschak和Andrews(1944),Nerlove1965年的專著,Intriligator1978年的教科書,Jorgenson1986年的綜述等;關于估計全要素生產率的經濟計量方法,可見Nadiri和Prucha2001年論文中的介紹。
目前全要素生產率國際比較研究以KLEMS項目最有影響。KLEMS項目是最近幾年由哈佛大學的Jorgenson教授和日本慶應大學的黑田教授等人共同倡議的國際間的全要素比較項目,K是資本(capital),L是勞動(labor),E是能源(energy),M是物質生產部門產生的中間投入要素(intermediate-input),S是服務生產部門產生的中間投入要素,即左邊是產出,右邊是生產總產值中的五個組成部分。這個等式中特別把能源提出來,就是為了將來好研究環境問題。KLEMS研究方法的基礎是雙國生產函數模型,并在這一模型框架下估計兩國之間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差距。這一方法最初由Jorgenson與西水(Jorgenson和Nishimizu,1978)提出并用于日本和美國的經濟增長因素的比較研究,并通過計算兩國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差距,來解釋國家之間在增長因素方面的不同。計算的理論基礎是微觀經濟學中的生產者理論和對偶理論。由于生產函數采用超越對數函數形式,對生產技術的描述可以限制在假設盡可能少的框架中(Christensen,Jorgenson,Lau,1971,1973)。這一方法可以利用指數的形式計算,也可以利用經濟計量學的方法計算(Jorgenson和Kuroda,1988;Jorgensonetal.1988)。這一分析框架已用在雙國與多國之間的比較,以及宏觀和產業部門之間的比較(Christensen,CummingsJorgenson,1980,1981;JorgensonandKuroda,1992;Conrad,1992)。在最初的研究中,生產函數是由增加值和資本、勞動等變量構成。在隨后的發展中,增加值改為總產值,在解釋變量中又包括了中間投入。
KLEMS項目目前已經形成了一個多機構參加的組合(ConsortiumProjectInstitutions),其中包括美國的4個機構(TheConferenceBoard,HarvardUniversity,BrookingsInstitute,FederalReserveBankofNewYork)和荷蘭、意大利、英國、德國、法國、西班牙、芬蘭、丹麥、加拿大、日本等國家的一些機構(Timmer,2000)。在亞洲區域,與此相似的項目ICPA(InternationalComparisonoftheProductivityamongPan———PacificCounties)也已接近完成,該項目包括日本、韓國、中國等國家和中國臺灣等地區。KLEMS項目研究的目的是:投入要素的變化對經濟增長、生產率和國際競爭力的影響,國家間增長的基本要素的區別,勞動力的質量與構成的變化與差異對國際競爭力的作用,國家之間高技術產業的生產率和國際競爭力的差異。
克魯格曼的批評其實有一個非常致命的錯誤。他引用Solow1957年所做的分析,認為在美國經濟增長當中,有80%以上是通過技術進步取得的,是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但是,Jorgenson等人1987年出版的書是根據Jorgenson和Griliches1967年文章之后研究方法進行研究的典范,該研究認為,美國從1948年到1979年的經濟增長因素分析中,資本是最重要的,勞動的貢獻是第二重要的,而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排在第三位。克魯格曼不可能不知道Jorgenson和Griliches1967年文章之后對全要素生產率研究的新發展,和Jorgenson等人1987年這本書的新結論,但是他仍然用了Solow1957年的結論。
2·經濟發展史研究的發現
在前面討論陳坤耀對克魯格曼批評的批評中提到技術進步包括與資本融合在一起的(embodied)和不包括資本投入的(disembodied)兩類。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取得技術進步的方式可能不同,發達國家所使用的技術處于國際技術的最前沿,發達國家的企業要取得技術創新,必須自己進行新技術的研發,而研發的投入在目前通用的生產率的研究中并不包括在投入要素內,依靠這種方式取得的技術進步屬于不包括資本投入的技術進步。與此相反,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以引進技術的方式取得技術創新,發展中國家引進的技術通常包括在新的機器設備里,屬于包括資本的技術進步。因此,以同樣的方式來研究一個國家不同的發展階段,那么,發展早期的全要素生產率將會較低,而達到發展階段后,全要素生產率將會較大,這個理論推斷在對美國和日本的經濟史研究中得到證實。
Hayami在其新著《發展經濟學:從貧窮到富裕》(DevelopmentEconomics:FromPovertytotheWealthofNations)的第5章主要討論了“經濟發展中的資本積累”的問題。該章介紹了Abramovitz(1993)的有關經濟史的研究,根據他的估算,對美國來說,在1800—1855年和1855—1890年間,全要素生產率對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貢獻要大大小于資本—勞動比例增長的貢獻,這說明在此期間,資本產出比例在增加。這一研究也大致證明了,在通常人們認為美國工業革命開始(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后的初期階段,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對日本來說,經濟史的研究也揭示了大致相似的增長類型。按照Hayami和Ogasahara(1995)的研究,如果假定日本的工業革命開始于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年代,在其后的工業革命的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也出現了資本—勞動比率的增長率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因此也同樣表明資本—產出比率的增長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只能解釋勞動生產率增長的10%,其余是投入要素的貢獻。日本的研究和美國的研究結果都表明,在隨后的工業發展的高級階段,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逐步提高,資本的份額在達到一個高點后開始下降。前面已經談過,克魯格曼對東亞經濟的分析所依據的實證研究之一就是Kim和Lau(劉遵義,1994)。而按照Hayami書中的分析,Kim和Lau(劉遵義,1994)的研究恰恰證明了東亞的4個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發展經歷顯示了與美國和日本早期發展相類似的增長模式。
三、小結:東亞經濟奇跡爭論對中國的意義
從格魯格曼挑起的這場“東亞經濟奇跡”爭論的回顧中,我們可以得到幾點對我國未來發展有意義的結論:
第一,全要素生產率的計算和經濟增長因素的分析具有一個嚴謹的理論體系和分析框架,如何從概念上正確把握特別重要。克魯格曼對東亞經濟奇跡的批評主要是對全要素生產率的經濟意義沒有正確把握,以及對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或地區在全要素生產率上的不同表現缺乏了解造成的。因此,我們不要簡單地根據克魯格曼對“東亞經濟奇跡”的批評來評論我國的經濟發展經驗,并作為討論我國未來經濟發展模式的依據。
第二,對于一個國家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來說,重要的是技術的不斷創新,而不在于全要素生產率的高低。從美國和日本等國家在未成為最發達國家之前,全要素生產率低,只有到了發達階段時全要素生產率才高的事實可以看出:這些國家在還處于發展中階段時,技術創新主要是靠從發達國家引進技術設備,只有到了發達階段各個產業的技術大多已經處于世界的最前沿時才轉而以不表現為資本的研發來取得技術創新。目前,我國還處于發展中階段,和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技術差距,要善于利用這個差距,在盡可能的范圍內引進合適的先進機器設備,這樣全要素生產率的水平雖然會較低,但是,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的速度反而會較快。
第三,我國雖然應該多利用引進技術來取得技術創新,但是,并不是就不用進行自主研發。首先,發達國家勞動力昂貴,發達國家的技術通常盡量自動化以減少勞動力的使用。我國勞動力相對便宜,從發達國家引進技術時,通常需要進行一些流程的研發創新,在不影響產品質量的前提下,應該盡量以勞動力來替代昂貴的自動化設備,這樣可以降低成本,增加效益。其次,有些產業我國有比較優勢,但是沒有比我國更發達的國家還留在這個產業里,因而也無法從其他國家引進時,或是,在這個產業里我國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只是最后一、二個關鍵的技術而難于從發達國家引進時,我國就需要在這樣的產業自己進行新產品和新技術的研發。秉持這兩個原則,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產業水平的提高,需要自主研發的領域將會越來越多,全要素生產率的水平也就會越來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