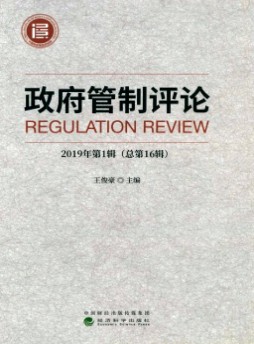政府危機管理與危機協(xié)同治理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政府危機管理與危機協(xié)同治理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我國正處于轉(zhuǎn)型期,正在經(jīng)歷著利益格局的調(diào)整、權(quán)力體系的變革、社會結(jié)構(gòu)的分化、人口流動的加劇等一系列變化,加之全球文化的交匯與碰撞,又引發(fā)了社會文化的激蕩、傳統(tǒng)思想觀念的嬗變等。所有這些劇烈的變化造成了社會不穩(wěn)定因素的增多,中國因而進入了危機頻發(fā)期。因此,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強調(diào)要“完善突發(fā)事件應(yīng)急管理機制”。實際上,及時、妥善而有效地治理危機已成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內(nèi)中國各級政府必須高度重視的重大挑戰(zhàn),能否處理好社會危機事件直接關(guān)系到政府在公眾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直接關(guān)系到中國的政治穩(wěn)定和經(jīng)濟發(fā)展,直接關(guān)系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gòu)建。綜觀我國危機治理的發(fā)展軌跡可以看出,它是一個由政府危機管理逐漸走向危機協(xié)同治理的過程。
一、陷入“國家或政府中心論”:中國危機管理的困境
在“9·11”事件影響下,經(jīng)歷了“非典”危機之后,危機管理已成為中國政府關(guān)注的重點和理論界研究的熱點。時至今日,在多方共同努力下,中國危機管理在理論與實踐上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這一點可從近年來危機管理諸多研究成果的涌現(xiàn)及《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應(yīng)急條例》、《國家突發(fā)事件總體應(yīng)急預案》的頒布與施行上反映出來。但由于中國危機管理理論研究起步晚,實踐經(jīng)驗不足,當前尚存在理論上的困境和實踐上的難題。有學者曾將當前國際危機管理的理論困境和實踐難題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在危機管理體制上,存在著“集權(quán)化”和“分權(quán)化”的結(jié)構(gòu)性矛盾;二是在危機溝通上,存在著危機信息公開與封閉的倫理性沖突;三是在危機管理路徑上,存在著經(jīng)驗主義與演繹主義的邏輯矛盾。還有學者將當前中國危機管理存在的問題概括為八個方面:危機意識淡薄;缺乏組織保障;各部門橫向協(xié)調(diào)不夠,資源共享程度低;對突發(fā)公共事件的監(jiān)測預警機制不健全;危情行政透明程度不夠;危機管理缺乏系統(tǒng)的戰(zhàn)略和政策規(guī)劃;缺乏法制保障;社會與公眾參與不夠。應(yīng)當說,這些分析有一定道理,但就當前中國危機管理而言,或難以簡單套用,或尚未抓住問題的關(guān)鍵。在筆者看來,從國家與社會關(guān)系的視角加以審視,當前中國危機管理理論困境與實踐難題的本質(zhì)或根本原因在于理論研究和實踐均陷入了“國家或政府中心論”的窠臼。
對于危機管理,用以指導全國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對工作的《國家突發(fā)事件總體應(yīng)急預案》中關(guān)于工作原則的第三條明確規(guī)定:“統(tǒng)一領(lǐng)導,分級負責。在黨中央、國務(wù)院的統(tǒng)一領(lǐng)導下,建立健全分類管理、分級負責,條塊結(jié)合、屬地管理為主的應(yīng)急管理體制,在各級黨委領(lǐng)導下,實行行政領(lǐng)導責任制,充分發(fā)揮專業(yè)應(yīng)急指揮機構(gòu)的作用。”在組織體系上,明確規(guī)定:“國務(wù)院是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急管理工作的最高行政領(lǐng)導機構(gòu)。在國務(wù)院總理領(lǐng)導下,由國務(wù)院常務(wù)會議和國家相關(guān)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急指揮機構(gòu)負責突發(fā)公共事件的應(yīng)急管理工作;必要時,派出國務(wù)院工作組指導有關(guān)工作。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區(qū)域突發(fā)公共事件應(yīng)急管理工作的行政領(lǐng)導機構(gòu),負責本行政區(qū)域各類突發(fā)公共事件的應(yīng)對工作。”由此可見,當前中國的危機管理是“以國家或政府為中心”的。這一點,也可從危機管理在中國理論研究和實踐中常被稱為“政府危機管理”這一點上得到佐證。這種“以國家或政府為中心”的危機管理必然會造成現(xiàn)實中危機管理主體單
一、社會力量參與不足等諸多問題,降低危機治理績效。必須指出,在危機治理機制中,政府毫無疑問應(yīng)占有主導地位。但是,危機不僅是對政府能力的挑戰(zhàn),更是對全社會整體能力的綜合考驗。沒有全社會的積極參與和大力支持,僅靠政府的力量,想圓滿地解決危機是不可能的。也正因為如此,有學者指出,“有效的危機管理需要政府、公民社會、企業(yè)、國際社會和國際組織的協(xié)作”。實際上,單一的治理機制存在著諸多問題。無論是國家、市場還是被許多人寄予厚望的公民社會,都無法單獨承擔應(yīng)對風險的重任,因為它們本身也是風險的制造者。若僅依靠國家或政府,會使危機的治理失效。
二、走出困境:革新危機治理范式與實現(xiàn)危機協(xié)同治理
既然中國危機管理的理論困境和現(xiàn)實難題的本質(zhì)或者說根源在于理論研究和實踐未擺脫“國家或政府中心論”的窠臼,那么,要走出困境,就必須跳出“國家或政府中心論”,實現(xiàn)危機治理范式革新。而要實現(xiàn)這種革新,首先要突破現(xiàn)有的理論視野,以一種科學的基礎(chǔ)理論指導實踐和理論研究。作為現(xiàn)代科學基礎(chǔ)理論的協(xié)同學理論和晚近興起的治理理論恰為我們提供了這種新的研究視角。
協(xié)同學是20世紀70年代聯(lián)邦德國斯圖加特大學理論物理學教授赫爾曼·哈肯創(chuàng)立的一門新興的系統(tǒng)學科。協(xié)同學即“協(xié)同合作之學”,它是一門以研究不同系統(tǒng)中存在的某種共同本質(zhì)特征為目的的綜合性橫斷科學。現(xiàn)代協(xié)同學理論認為,那些“與外界有著充分物質(zhì)與能量交換的開放系統(tǒng),它們從無序到有序的演化都遵循著共同的規(guī)律,即在一定條件下,由于構(gòu)成系統(tǒng)的大量子系統(tǒng)之間相互協(xié)同的作用,在臨界點上質(zhì)變,使系統(tǒng)從無規(guī)則混亂狀態(tài)形成一個新的宏觀有序的狀態(tài)”。可見,協(xié)同即“相互協(xié)調(diào)、共同作用”,它有助于整個系統(tǒng)的穩(wěn)定和有序,能從質(zhì)和量兩方面放大系統(tǒng)的功效,創(chuàng)造演繹出局部所沒有的新功能,實現(xiàn)力量增值。它反映了系統(tǒng)中各子系統(tǒng)之間結(jié)合力的大小和融合度的高低,是辯證唯物主義量變引起質(zhì)變哲學理論的生動體現(xiàn)。
“治理”則是近年來國際社會科學中最時髦的術(shù)語之一。關(guān)于“治理”概念的界定,學界意見紛呈。在眾多關(guān)于治理的定義中,聯(lián)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定義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權(quán)威性。該委員會在1995年發(fā)表的一份題為《我們的全球伙伴關(guān)系》的研究報告中對“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機構(gòu)和個人管理其共同事務(wù)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diào)和并且采取聯(lián)合行動的持續(xù)的過程。它既包括有權(quán)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guī)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個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規(guī)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治理過程的基礎(chǔ)不是控制,而是協(xié)調(diào);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涉及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xù)的互動。”簡言之,“治理是官方的或民間的公共管理組織在一個既定的范圍內(nèi)運用公共權(quán)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種不同的制度關(guān)系中運用權(quán)力去引導、控制和規(guī)范公民的各種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
基于協(xié)同學理論和治理理論,筆者認為,在強調(diào)政府在危機管理中的作用的同時,必須最大可能地調(diào)動社會資源,努力拓寬社會參與渠道,形成全民動員、集體參與、共渡難關(guān)的局面,群防群治,協(xié)同合作應(yīng)對危機,構(gòu)建社會整體的危機應(yīng)對網(wǎng)絡(luò),實現(xiàn)危機協(xié)同治理。這里,危機協(xié)同治理是指在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和信息技術(shù)的支持下,政府、非政府組織、企業(yè)、公民個人等社會多元要素參與合作,相互協(xié)調(diào),針對潛在的和當前的危機,在危機發(fā)展的不同階段采取一系列的控制行動,以期有效地預防、處理和消弭危機,最終達到最大限度地維護和增進公共利益的目的。具體來說,有如下四層內(nèi)涵:一是危機治理主體的多元性。除了政府之外,包括非政府組織、企業(yè)、家庭、公民個人在內(nèi)的所有社會組織和行為者都是危機治理的參與者。二是治理權(quán)威的多樣性。危機協(xié)同治理需要權(quán)威,但這個權(quán)威并非一定是政府,其他主體也可以在危機治理活動中發(fā)揮和體現(xiàn)其權(quán)威性。三是強調(diào)各主體之間的自愿平等與協(xié)作。政府不只是依靠強制力,而是需要通過政府與非政府組織、政府與企業(yè)、政府與社會團體之間的協(xié)商對話、相互合作來建立伙伴關(guān)系,共同治理危機。四是危機協(xié)同治理的直接目的是有效地預防、處理和消弭危機,最終目的是最大限度地維護和增進公共利益。
在危機協(xié)同治理過程中,政府、非政府組織、企業(yè)、公民個人等主體能夠充分利用各自的資源、知識、技術(shù)等優(yōu)勢,在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和信息技術(shù)的支持下,發(fā)揮出對危機治理“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功效。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指出的那樣:“許多人協(xié)作,許多力量融合為一個總的力量,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造成‘新的力量’,這種力量和它的一個個力量的總和有本質(zhì)的差別。”因此,危機協(xié)同治理可以說是危機治理的理想范式。就當前我國危機治理的現(xiàn)實狀況和未來需求來看,革新危機治理范式,實現(xiàn)危機協(xié)同治理,應(yīng)從以下五個方面著力:完善危機協(xié)同治理的法規(guī)制度,優(yōu)化危機協(xié)同治理的權(quán)責體系,加強危機協(xié)同治理的資源保障,搭建危機協(xié)同治理的信息平臺,培育危機協(xié)同治理的社會資本。令人欣慰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fā)事件應(yīng)對法》幾經(jīng)修改,已于2007年8月30日由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細讀該法,可以發(fā)現(xiàn),該法在強調(diào)政府在應(yīng)對突發(fā)事件中的責任、地位和作用的同時,明確規(guī)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有義務(wù)參與突發(fā)事件應(yīng)對工作”,注重構(gòu)建社會整體的突發(fā)事件應(yīng)對網(wǎng)絡(luò)。從這個意義上講,該法的出臺標志著我國危機管理邁出了從“以政府為中心”的危機管理或“政府危機管理”向“危機協(xié)同治理”轉(zhuǎn)向的步伐。